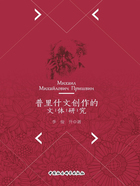
第一章 普里什文研究现状综述
普里什文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引起了成千上万读书人的强烈共鸣。在俄罗斯这个热衷于读书的国度里,从1973年以后的40多年中就举办过多次大型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
1973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纪念普里什文100周年诞辰创作大会;
1989年秋明普里什文作品学术研讨会;
1991年、1992年、1993年莫斯科普里什文作品学术研讨会;
1993年叶列茨洛扎诺夫作品学术研讨会;
1991年、1992年、1993年莫斯科大学普里什文作品学术研讨会;
1992年秋明大学普里什文作品学术研讨会;
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普里什文作品学术研讨会;
2002年叶列茨国立布宁大学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29周年创作遗产大会;
2003年叶列茨国立布宁大学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30周年创作遗产大会。
为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35周年,2008年莫斯科州塔尔托姆区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晚会,普里什文于1922—1925年曾在塔尔托姆区生活,在此写了几篇短篇小数和题为“矮腰皮鞋”的随笔。在他的领导下,塔尔托姆区开始出版《矮腰皮鞋》的杂志。
为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40周年,2013年3月15日至9月15日在俄罗斯的精神中心——谢尔吉耶夫自然保护区博物馆(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духовный центр России)东楼的“马苑”举办了题为“春之光”的展览。展览期间,还召开了题为“20世纪文化中的普里什文:纪念140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研究普里什文创作的大专家、博物馆工作者、民俗学家和高校教师。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议题:“普里什文和洛扎诺夫”“自然与创造:普里什文和帕斯捷尔纳克”“普里什文30年代的日记和照片呈现的扎果尔斯克”“普里什文与切尔尼戈夫斯卡—戈夫西曼斯基的隐修区:1920—1930年”“克里奇科夫和普里什文”“普里什文1926—1929年的作品、日记和照片所呈现的谢尔吉耶夫市和郊区”等。参加会议的代表还观看了关于普里什文家族的纪录片,大家一致表示,“应在谢尔吉耶夫镇建立一座普里什文纪念碑”。

春之光(普里什文照片)

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40周年的展览宣传画
为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45周年,利佩茨克州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2018年1月26日,利佩茨克州方志博物馆举办了“生命循环圈”的摄影展;2月5日在叶列茨第一中学召开了题为“普里什文与利佩茨克区:纪念作家诞辰145周年”的学术会议;2018年3月1日在斯摩棱斯克州图书馆召开了面向中学生的题为“他与大自然同呼吸”的学术会议;为纪念普里什文诞辰145周年,俄罗斯作家协会诺夫哥罗德区域分会举办了题为“大自然的守护者”的文学竞赛活动。
俄罗斯学术界在召开讨论普里什文创作的全俄学术会议之后,有时会出版一些很有思想深度和学术史建设意义的会议文集和专著,如《普里什文与二十世纪的宗教哲学思想》《普里什文:创作遗产研究的迫切问题:纪念作家诞辰129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资料》(第一辑、第二辑)、《普里什文:创作遗产研究的迫切问题:纪念作家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资料》(第一辑、第二辑)等。
四十多年来举办过多次普里什文作品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但这并不是说对普里什文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就始于四五十年之前。实际上,普里什文刚一登上文坛,就被评论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眼看中。在20世纪初的文坛,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是一位著名评论家。在普里什文1907年发表处女作《鸟儿不惊的地方》、1908年发表《跟随魔球走远方》后,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1911年率先撰写了《伟大的潘——论米·普里什文的创作》一文:“米·普里什文是一位已经形成了的、完善的艺术家……他之所以完美,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形式、自己的风格……有一个主题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这一主题就是——伟大的自然守护神。他想解决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与你生活期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些民族学专著和旅行笔记;但这仅仅是画面的底色。全部的实质还在于作者面对‘自然’时的那些最亲切的感受。”[1]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眼光极为敏锐,在俄罗斯是他第一个准确地捕捉到了普里什文创作的核心内容和艺术价值,那就是“他与自然的最亲密的联系”。从此,“伟大的自然守护神就成为普里什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最准确的概括之一”。
勃洛克是20世纪初彼得堡一位极受公众尊敬的大诗人。彼得堡甚至流行这么一个神话:“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哪一位妙龄女子还不倾心勃洛克的”[2]。勃洛克与安德烈·别雷、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被尊称为“小一辈儿”象征主义诗人的三大代表。勃洛克这位大诗人以他与生俱来的诗人的洞察力极早就发现了散文大师普里什文创作的本质。他在与普里什文一次谈话中说:“这当然是诗,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韵味”[3],而普里什文当时只发表了《鸟儿不惊的地方》和《跟随魔球走远方》这两部作品。
高尔基早在1911年就喊出20世纪初的最强音,他在1911年9月写给《公众杂志》编辑В.С.米拉留波夫的信中赞叹道:“普里什文的《跟随魔球走远方》简直是棒极了。”[4]时隔15年后的1926年,高尔基在致普里什文的信中又情不自禁地赞扬说:“就该像您这样来写作!”
普里什文之所以名声远播,首先是因了高尔基这位文化巨人前后20多年的大力培养、精心爱护、热情鼓励、奖掖和提拔,其次是普里什文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蕴含的魔力,是他本人的内因和内功起了极为主要的作用。
1912—1914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普里什文文集》三卷本。
在普里什文学的研究史上,评论家尼·扎莫什金功不可没。他在20世纪20年代相继写了《普里什文的创作》(1925年)、《别连捷伊王国的作家》(1927年)、《个性化的和非个性化的》(1929年)。
1930年是普里什文评论中不同寻常的一年。此后,对普里什文评论的风向开始有所变化。这一年,А.叶夫廖明和米·格里戈里耶夫对普里什文提出批评,指责普里什文逃往大自然,远离社会生活,远离政治,而20世纪30年代,普里什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杰作:《金角》(1932年)、《人参》(1932年)、《我的随笔》(1933年)、《灰猫头鹰》(1938年),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国家大道》第一部。
苏联文学界开始重新真正关注普里什文的创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从各个视角论述普里什文创作的副博士和博士论文:康·希洛娃的《普里什文的创作道路》(1954年)、扎尔欣的《米·普里什文1907—1928的创作》 (1957年)、哈依洛夫的《普里什文的创作》(1959年)、伊·莫加绍夫的《米·普里什文的艺术技巧(40—50年代的创作)》(1961年)、В.К.普多日戈尔斯基的《米·米·普里什文的短篇和中篇小说(1920—1953)》(1963年);Г.А.沙别尔斯卡娅的《米·普里什文1905—1917年的创作》(1964年);В.В.斯塔丽娅洛娃的《米·普里什文的创作方法——论作家的思想、美学观问题》(1969年)等。一批很有学养的学者撰写了一些很有思想深度的专著,如赫梅尔尼茨卡娅的《普里什文的创作》(1959年)、哈依洛夫的《普里什文的创作道路》(1960年)、伊·莫加绍夫的《普里什文》(1965年)。在普里什文1954年去世后,新版的普里什文六卷文集于1956—1957年出版。在这部文集里,第一次收入了《杉木林》《大地的眼睛》《我们时代的故事》《国家大道》,第一次发表了作家晚年时期的日记(1951—1954年,有删减)。
普里什文的遗孀瓦·德·普里什文娜1957年出版了他战争年代的日记摘录。1960年出版了根据普里什文生活的不同年代的日记所编成的《勿忘草》和《真理的童话》。瓦·德·普里什文娜又根据普里什文生活的不同年代的日记中的创作谈片段整理成了很有影响的《来龙去脉》(1974年)、《我们的家园》(1977年)、《生活的循环往复》(1981年)、《通往语言之路》(1985年)等著作。
1973年2月,列宁格勒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举办了纪念普里什文100周年诞辰全苏创作大会。在大会上,瓦·科日诺夫振臂一挥:“普里什文的时代到来了!”
这一句是抒情,是呼喊,是赞誉,语气铿锵有力,字词掷地有声,因为,这声音里的语调慷慨激昂,语气十分肯定,令人内心再也不可能不信服普里什文的创作了。
这一声惊呼之后,苏联研究界对普里什文创作遗产的研究便在全方位展开。
20世纪80年代是普里什文创作研究中硕果累累的年代。在80年代,具有总结和标志意义的大型出版工程是瓦·科日诺夫领导下筹划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新版的普里什文八卷文集。八卷集的出版筹划者——瓦·科日诺夫、利·亚·梁赞诺娃、亚·格里申娜等确实功不可没。
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制定了很明确的工作规划,即下一步如何对待普里什文的文学遗产:①对鲜为人知的和未发表的资料进行鉴定,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期间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书信、作家履历资料;②对普里什文重大作品的创作史料进行综述,主要指的是《人间苦难》《恶老头的锁链》《人参》《叶芹草》《太阳的宝库》《我们时代的小说》《杉木林》《国家大道》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另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语言、词汇学、句法学和修辞学角度,甚至小到对普里什文的文学作品的动词词源派生模式专门进行比较研究。1981年,奥廖尔国立师范学院的博士科列斯尼科娃撰写了《词源派生模式:普里什文文学作品语言与现代俄罗斯规范标准语中的动词比较分析》。过了几年,科斯久克撰写了《学术与艺术文本中的词语:词汇意义的功能方面》的专著(1987年)。谢洛娃撰写了《普里什文艺术创作语境中的方言词汇》的专著(1988年)。一些研究者如阿格诺索夫、格里芙尔特女士开始探讨普里什文的创作方法问题。阿格诺索夫出版了《普里什文的创作和苏联哲理小说》(1988年)和《苏联哲理小说》(1989年)。一些研究者开始梳理普里什文各个时期的创作中的不同体裁特征,如阿格诺索夫、格里芙尔特、А.Н.多福山、А.А.泽姆连科夫斯卡娅、Н.В.雷巴年柯、雪尔茨·伍铁、А.В.尤尔塔舍娃。一些研究者如З.Я.霍洛托娃、格里芙尔特开始对比普里什文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和现实主义成分、叙事成分和抒情因素。还有一些学者研究普里什文的极具个性化的诗学问题:不出场(藏而不露的)的叙述人、颜色的象征意义、艺术时间等。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还有一些实力极为雄厚的研究者大胆地开始对普里什文的整个创作道路,对他的哲学、伦理和美学观的整个复杂体系进行挖掘,如В.库尔巴托夫的《米·普里什文》(1986年)、西涅科《普里什文创作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形象体系特点》(1986年)、阿格诺索夫的《普里什文的创作和苏联哲理小说》 (1988年)、弗洛罗娃的《当代苏联散文中的普里什文传统》(1986年)、格尔基延柯的《普里什文与维尔纳茨基》 (1988年)。在80年代末,格·加切夫的力作《三位思想家:列昂季耶夫、洛扎诺夫、普里什文》(1988年)中的“俄罗斯沉思录章节”(1990年)也很重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普里什文的创作研究开始往纵深方面发展。1990年,奥廖尔国立师范学院的副博士亚布拉科夫撰写了《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学中自然与人相互关系的艺术思考:列昂诺夫、普拉东诺夫、普里什文》,率先展开了对普里什文创作的平行比较研究。在90年代及此后的20多年里,普里什文研究中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就成了一根主线。1993年,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的博士克里莫娃撰写了《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的布宁和普里什文创作》。纳·德瓦尔佐娃博士1993年在《文学问题》杂志第3期发表了《普里什文与梅列什科夫斯基(关于隐没城的对话)》。此后,纳·德瓦尔佐娃开始挖掘普里什文与同时代作家——更准确地说是普里什文与文学导师之间的精神文化联系。1993年,她在莫斯科大学通过了《普里什文的创作道路与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博士论文答辩。
20世纪90年代的平行比较研究成果还有库尔梁茨卡娅的《普里什文与屠格涅夫》、格里芙尔特的《普里什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基谢廖夫的《普里什文与20世纪初的俄罗斯作家》、希洛娃的《普里什文与扎波洛茨基》、亚布拉科夫的《普里什文——列昂诺夫——普拉东诺夫》、科涅科娃1998年的《普里什文与科涅科夫创作中的自然诗学—文化比较分析》。
90年代除了普里什文与艺术家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外,一些研究者对其他问题也进行研究,如格里芙尔特1992年在位于叶卡捷林堡的国立乌拉尔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创作中的自然情感》的博士论文答辩。塔基丽采娃1994年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散文中的象征》的副博士论文答辩。索科洛娃1997年通过了题为《20世纪前20年普里什文散文中描写自然的哲学角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安年科娃1997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艺术政论专著的修辞句法特点》的博士论文答辩。波波娃1998年在国立坦波夫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40—50年代散文中的人文主义理念:结构诗学角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胡坚柯1998年在国立巴尔瑙尔师范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艺术体系中的“创作行为观”》的副博士论文答辩。1998年,在纳·德瓦尔佐娃教授和普里什文故居博物馆梁赞诺娃馆长的努力下,秋明“向量—布克”出版了一本题为《普里什文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的文集。托卡列娃1999年在国立哈巴洛夫斯克师范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艺术世界中的神话原型因素和童话幻想成分》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多琴柯1999年在莫斯克国立开放师范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日记中的反义现象诗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1991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宣布在几年内出齐普里什文的全部日记。
2000年,奥·亚·马什金娜在托姆斯克大学通过了题为《时代文学哲学语境下的普里什文小说〈国家大道〉》的副博士论文答辩(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Машкина:《Роман М.М.Пришвина〈Осударева дорога〉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эпохи》,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 Томск)。同年,塔·阿·斯捷潘诺娃在萨马拉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描写卡累利阿和俄罗斯北国的作品中的卡累利阿方言词汇》的副博士论文答辩(Татья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их говоров Карелии в произведéниях М.М.Пришвина о карелии и русском севере》,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амара)。莫斯科的尼·尼·伊万诺夫通过了题为《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普里什文艺术世界里的古斯拉夫神话》的博士论文答辩(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ванов:《Древн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ческий миф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мире М.Горького,А.Н.Толстого,М.Пришвина》,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Москва)。季·霍洛托娃于2000年在伊万诺沃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普里什文的艺术思维:内容·结构·语境》的专著。
2001年,叶列茨国立布宁大学教授纳塔利娅·鲍里索娃出版了力作《普里什文创作中的神话生活》。在阿尔马维尔国立师范学院举办的题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迫切问题”研讨会上,巴芙洛娃做了题为“普里什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的个性艺术观”的发言。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大学的亚·亚·迪尔金通过了题为《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哲理化散文:思想的象征意义》的博士论文答辩(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ырдин:《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óфская проза после 1917 года,символика мысли》,дó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áция. Ульяновск)。
2002年,在阿尔马维尔国立师范学院举办的“科日诺夫遗产和评论、文艺学、史学、哲学的迫切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上,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郭利老师做了题为“普里什文和庄子创作中的自然观”的报告;巴芙洛娃做了题为“普里什文和科日诺夫是如何理解个性的?”的发言。
2003年,别尔哥罗德州的舍米亚金娜通过了《布宁和普里什文日记中的人与世界》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最近20多年来,著名作家阿·瓦尔拉莫夫先后在《文学学习》《文学问题》《十月》和《新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述普里什文创作的文章。他于2003年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日记和艺术散文中的生活是创造》(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арламов:Жизнь как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дневнике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е М.М.Пришвина,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áция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的博士论文答辩。他把所有研究成果汇总在一起,写成了《普里什文》一书,于2003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列入高尔基当年创办的名人传记丛书出版。
2004年,纳·德瓦尔佐娃教授在《文学问题》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跨地域的作家(论普里什文的文学声望)》。在同一期的《文学问题》上还有尤里·洛扎诺夫的《列米佐夫的普里什文神话》。俄罗斯文学界在研究普里什文的早期日记方面获得重大进展。远东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伊·诺沃谢洛娃出版了《普里什文的“日记”——精神宇宙》(Ирина Германовна Новоселова:《Дневники М.М.Пришвина:духóвный космос》.Монография,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та,2004)一书。乌法市诺沃库兹涅斯克东方大学的奥·亚·马什金娜(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Машкина)出版了《文本语境和阐释(俄罗斯宇宙主义散文)》一书。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大学的亚·亚·迪尔金(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ырдин)出版了《20世纪普里什文和列昂诺夫哲理化散文中的精神因素和美学情感》一书。秋明市的叶·阿克瓦兹芭通过了《艺术文本中词语的外延和内涵意义(普里什文作品中植物和动物界语汇采英)》(Екатерина Омаровна Аквазба:Денотативное и коннот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ексте: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лексики растительного и живóтного мира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М.М.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Тюмень)的副博士论文。
наук.-Тюмень)的副博士论文。
2005年,旅美的塔·马·鲁达舍芙斯卡娅(Тасия Матвеевна Рудавшевская)出版了《普里什文与俄罗斯经典·叶芹草·国家大道》一书。尤·谢·莫赫马特金娜在国立弗拉基米尔师范大学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和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自然哲学》(Юлия Сергеевна Мохнаткина:《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М. Пришвина и А.П.Платонова》,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Владимир)的副博士论文答辩。米丘林斯克市的阿·阿·泽姆丽娅科芙斯卡娅(Азал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Земляковская)出版了专著《普里什文袖珍散文文集里的体裁结构特色》。莫斯科市的奥·亚·科维尔申娜通过了《普里什文艺术意识中的时间和永恒辩证关系》(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выршина:Диалектика времени и вечности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Михаила Пришвина)的副博士论文答辩。2005年年底,由普里什文故居博物馆馆长梁赞诺娃和副馆长格里申娜合编的《普里什文个人档案》一书出版。
2006年,萨马拉市的安·米·科里亚金娜通过了《普里什文散文中日记文体的叙述特色》 (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ядина:Специфика дневниковой формы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прозе М.Пришвина)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莫斯科市的尤·伊·奥丽霍芙斯卡娅(Юлия Ивановна Ольховская)通过了《普里什文散文文体的演变:从袖珍体到大背景语境抒情体》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07年,亚·姆·博多克肖诺夫在《俄罗斯文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普里什文世界观和创作中的普列汉诺夫》一文。
2008年,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亚·姆·博多克肖诺夫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创作的哲学世界观话语和文化背景》 (А.М.Бодоксёнов:Философско-мировоззрéн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и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М.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доктора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Белгор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Белгород)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
2009年,语文学副博士马·格·丘柳金娜通过了题为《日记是政论体裁:直观—功能特点》 (М.Г.Чулюкина:Дневник как жанр публицистики:предмет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0年,在国立叶列茨布宁大学和国立科斯特罗马涅克拉索夫大学支持赞助下,А.М.博多克肖诺夫推出了专著《米·普里什文和瓦·洛扎诺夫:创作对话的世界观背景》。2010年,语文学副博士维·阿·乌尔维洛夫通过了《20世纪20年代描写革命小说的结构诗学:魏列萨耶夫的〈在死胡同〉、阿索尔金的〈西府采夫—弗拉热克胡同〉、普里什文的〈人间苦难〉》 (Вячеслав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Урвилов:Поэтика композиции романов о революции 20-х гг.XX в.:“В тупике”В.В.Вересаева,“Сивцев Вражек”М.А.Осоргина,“Мирская чаша”М.М.Пришвина)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语文学副博士尤·维·布尔达科娃通过了题为《作家日记是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现象:体裁类型和体裁诗学》 (Юлия Вячеславовна Булдакова: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 как феномен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1920-1930-х гг.:типология и поэтика жанра)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1年,语文学副博士帕·阿·易卜拉吉莫娃通过了题为《以米·普里什文和瓦·普里什文娜的爱情日记〈我们俩〉为基础考证作家眼中世界图景的文化概念场》 (Патимат Абдулмуминовна Ибрагимова:Конце птосфера авторск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дневников М.М. Пришвина и В.Д.Пришвиной“Мы с тобой:дневник любви”)的副博士论文答辩。2011年,语文学副博士柳·瓦·弗罗洛娃通过了题为《米·普里什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中的原质要素(水、气、土、火)概念》(Любовь Васильевна Фролова:Концепты первостихий—вода,воздух,земля,огонь в романе“Кащеева цепь”М.М. 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á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库班国立大学语文学副博士阿·尤·帕夫洛娃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苏维埃时期作品中的个性艺术观和个性生成的道德哲学背景》 (Анастасия Юрьевна Павлова:Худóжествен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личности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контексты ее становлéния в прозе М.М.Пришви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 Кубан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Армавир)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2年,语文学副博士纳·伊·利绍娃通过了题为《米·普里什文艺术话语中的旅行主题》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Лишова:Мотив стрáнствий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дискурсе М.М.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语文学博士叶·阿·胡坚科通过了题为《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曼德里施塔姆、左琴科、普里什文的艺术人生是一种后继文本书写》 (Е.А.Худенко:Жизнетвóрчество Мандельштама,Зощенко,Пришвина 1930-1940-х гг.как метатекс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3年,叶列茨国立布宁大学谢·维·洛格维年科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长篇小说〈国家大道〉的艺术空间结构》(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огвиненко: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стрáнства в романе М.М.Пришвина“Осударева дорог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 Елец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И.А.Бунина.-Елец)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5年,叶列茨国立布宁大学奥·尼·杰尼索娃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日记和艺术话语中的爱情形而上学》 (Олес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Денисова:Метафизика любви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м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дискурсе М.М. 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Елец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И.А.Бунин.-Елец)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沃罗涅日国立大学伊·伊·斯特拉霍夫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艺术文本中地名空间的自传体意境》 (Игорь Игоревич Страхов: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зм  прострáнства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ах М.М.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прострáнства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ах М.М.Пришвина,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наук Воронёжского гос.унниверситета.-Воронеж)的博士论文答辩。
наук Воронёжского гос.унниверситета.-Воронеж)的博士论文答辩。
2017年,在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北方极地联邦大学的奥·弗·波斯佩洛娃通过了题为《20世纪初北方叙事散文的神话诗学:列米佐夫、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恰佩金》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Поспелова:Мифопо-этика прозы север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А.М.Ремизов,Е.И. Замятин,М.М.Пришвин,А.П.Чапыгин,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еверного(Арктического)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Архангельск)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2019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叶·尤·科诺列通过了题为《普里什文1900—1930年创作中的“通往隐没城之路”的情节》(Е.Ю.Кнорре:Сюжет“Пути в невидимый град”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Пришвина 1900-1930)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普里什文的18卷日记前后历经27年,先后辗转四家出版社终于于2017年全部出齐,这对研究他的创作全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界对普里什文的译介始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评论和研究是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世界文学》杂志1980年发表了非琴翻译的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潘安荣翻译的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此后的40多年,许贤绪在《中国俄语教学》发表了《当代苏联生态文学》一文。杨传鑫在《江汉学术》发表了《自然精神的赞美诗—读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一文(1991年)。李俊升在《国外文学》发表了《我写——我在爱:大自然的歌者米·米·普里什文》(1995年)。傅璇在《俄罗斯文艺》发表了《依照心灵的吩咐——读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一文(1998年)。杨怀玉在《国外文学》发表了《一份写给心灵的遗嘱——普里什文研究概论》一文(2002年)。姚雅锐在《贵州社会科学》发表了《森林之魂与草原之灵——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与中国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生态作品比较研究》。姚雅锐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自然中的人性与人性中的自然——论普里什文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一文。马晓华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自然与人的神性感应—满都麦与普里什文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一文。张鑫在《北方文学》(下旬)发表了《浅论普里什文的“自然与人”创作思想》一文。杨怀玉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了《在隐没的城墙边——普里什文研究概述》一文。王国勇在《汉语言文学研究》发表了《从“熊”这面镜子里……——〈一对老熊〉赏析》一文(2003年)。王加兴在《当代外国文学》发表了《人应该是幸福的——评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一文(2004年)。止庵在《出版广角》发表了《热爱大自然的人》一文(2006年)。刘敏娟在《南昌大学》发表了《论苏联生态文学的历史轨迹和特征》一文(2007年)。河南大学的魏征发表了《米·米·普里什文创作中的自然主题》一文(2008年)。王淑杰在《山东文学》发表了《剖析普里什文作品中的和谐生态思想》一文(2009年)。王学、权千发在《科技信息》发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普里什文和孙犁的生态文学之比较研究》一文。李明明在《环境科学与管理》发表了《浅析普里什文和谐生态理念》一文。郭茂全在《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发表了《自然美的话语镜像与生态善的精神和弦——论米·普里什文的生态散文》一文。绿窗在《当代人》发表了《生灵的盛宴》一文。刘文飞在《俄罗斯文艺》发表了《普里什文三题》一文。张鹏在《阅读与写作》发表了《普里什文:倾心自然守望大地》一文(2011年)。姚雅锐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了《试析普里什文作品中蕴涵的生态良知》一文(2012年)。山西大学的胡晋豫发表了《普里什文创作中的乌托邦思想研究》一文(2012年)。李俊升在《俄罗斯文艺》发表了《普里什文的随笔创作论——以〈鸟儿不惊的地方〉为例》一文(2015年)。黄彦彦在《语文学刊》(教育版)发表了《生态人物结构构建——蒙古族生态文学与俄罗斯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物世界之比》(2015年)。李艳在《德州学院学报》发表了《一曲人性的悲歌——普里什文〈猎犬安查儿〉解读》一文。杨素梅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了《论普里什文随笔中的自然主题》一文。刘文飞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一文。李勇在《江苏社会科学》发表了《普里什文作品中的生态文学思想及其浪漫主义气质》一文(2013年)。周湘鲁在《人与生物圈》发表了《俄罗斯老虎文学赏析》一文(2014年)。杨琳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一文。王霆在《七彩语文(教师论坛)》发表了《心灵与自然的吻合——〈林中小溪〉的生态学解读》一文。魏征在《安徽文学》(下半月)发表了《试论普里什文作品中爱的主题》一文。王奉安在《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发表了《“绿色作家”普里什文》一文。杨敏在《中国校外教育》上发表了《〈大自然的日历〉中季节的启示》一文。古耜在《辽河》上发表了《倾心于不言的大美》一文。张宇在《名作欣赏》上发表了《亲人般的关注,大自然的眼睛——生态美学视阈下普里什文作品思想研究》一文。黑龙江大学的王艳男发表了《论普里什文创作中的世界图景》一文。古耜在《海燕》上发表了《散文的诗性》一文。王奉安在《气象知识》发表了《与大自然为伍的“绿色作家”》一文。杨敏在《文学教育》发表了《〈恶老头的锁链〉中的神话母题》一文。郭利在《俄语学习》发表了《普里什文及其创作》一文。廖全京在《四川文学》发表了《青葱回归路——从普里什文到利奥波德》一文(2016年)。舒坦在《文学教育》发表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长的日记发行》一文(2017年)。王佳在《学术交流》上发表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先行者——评〈鸟儿不惊的地方〉》一文(2018年)。
中国出版的一些学术专著对普里什文的创作和生活分专章和专节展开了研究和论述,包括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1992年)、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1994年)、李明滨主编《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史》(1994年),还有《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俄罗斯卷)》(1999年)中李俊升撰写的专章、彭克巽在《苏联小说史》(1988年)中的论述、严永兴在《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一文中的简要介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非琴翻译的《普里什文随笔选》。陇塬大地的李业辉在普里什文精神和气质的熏陶下,创作了散文集《爱是人生的愿望》(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和《岁月随想》(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杨怀玉通过了《论普里什文“人与自然”的创作思想》的博士论文答辩(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普里什文选集五卷本译文集:《鸟儿不惊的地方》《恶老头的锁链》《大自然的日历》《人参》《大地的眼睛》。2006年,杨素梅、闫吉青出版了《俄罗斯生态文学论》。李俊升2007年通过了《论普里什文创作的文体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潘安荣老师翻译的《普里什文散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刘文飞研究员撰写的《普里什文面面观》一书。李俊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0日)发表了题为《顺应自然规律 重视人文关怀——普里什文与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的遥感》一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了南京大学石国雄教授翻译的《大自然的日历》《有阳光的夜晚》《飞鸟不惊的地方》《亚当与夏娃》和《林中水滴》。
在掌握了对普里什文创作的研究现状之后,笔者选择他创作的文体创造作为研究对象。本专著由引言、研究资料综述、九个专章、结束语和参考资料组成。在研究普里什文的独特文体艺术时,自始至终关注的重心是其文体创造中体裁的繁丰性、语体的创新性和风格的独特性。这就是专著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创新之处。引言中阐述了专著的研究题目、现实意义、撰写专著的目的、任务和学术创新价值。
[1] 米·普里什文:《鸟儿不惊的地方》,冯华英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转引自Людмила Егоровна Тагильцева.《Символ в прозе М.М.Пришвина》.С.3。
[2] Соломон Волков.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Санкта-Петербурга с основáния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01.С.162-163.
[3] Собранию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М.Пришвина.Том 1.С.801.
[4] 《Горький.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Под ред.С.Д.Балухатова и В.А.Десницкого.М.-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1941.С.70.Цит.по:Собранию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М.Пришвина.Том 1.С.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