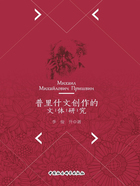
引言
普里什文是20世纪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
普里什文的艺术创作体裁繁丰、语言优美、风格独特。他素以写随笔、童话故事、散文、散文诗、中短篇小说和日记而闻名于世。他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人间苦难》《恶老头的锁链》《人参》《国家大道》和《杉木林》等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他的创作谈《大地的眼睛》和《仙鹤的故乡》等为世界文论史贡献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果把他的创作遗产放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背景中来观照,他与任何作家都绝不混淆也不重复。
普里什文的美文美得绚丽多彩,美得惊世骇俗。他的美文是早已被世人公认了的,他的美文不惧怕争议和挑战。就连20世纪的文化巨人高尔基都觉得普里什文“无一字不秀雅”,他在1926年撰文论普里什文时也有些为难,不敢轻易下笔:“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要写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就应该像您一样这么精湛娴熟地来写,可我也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1]。“整个俄罗斯文学都是在言说着痛苦。您是唯一一位俄罗斯作家,想方设法用哪怕一个词儿来张扬欢乐。这是很困难的,也不是马上能被理解的。”[2]普里什文也欣然并及时做了回应:“普天同乐这门最为艰深的学问是艺术家的必修课”[3]。帕乌斯托夫斯基对此做了确认:“普里什文的作品,是层出不穷的发现的无穷无尽的欢乐”[4]。
博大精深如高尔基者在致函普里什文时斩钉截铁,一锤定音,既是概括,也是结论。即使没有读过普里什文的美文,也会由此对他的美文之美深信不疑。高尔基再三强调,这不是他故意谦虚,也不是他有意矫情,更不是他想要恭维,而是他内心确实承认自己难以望普里什文之项背。其实,高尔基早在1911年就喊出了20世纪初的最强音:“普里什文的《跟随魔球走远方》简直棒极了”。

高尔基——普里什文的文学导师
普里什文生于长于孕育了上百位文化艺术和科技名人的俄罗斯中西部黑土地带奥廖尔州。奥廖尔是俄罗斯的心脏,是俄罗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奥廖尔州及其方圆几百公里这片肥沃的黑土拥有的水土地脉,得天独厚。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皮萨列夫、丘特切夫、费特、布宁、魏列萨耶夫、安德烈耶夫、扎依采夫、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诗人戈洛捷茨基、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等文化巨人,这一片土地也因这些文化巨人而变成一方人杰地灵的名人故乡。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正如研究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不研究屠格涅夫是不可饶恕一样,同样,阅读欣赏体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是一定要深入研究普里什文的。没有读过普里什文的美文就不算真正意义上读过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普里什文与洛谢夫、巴赫金、利哈乔夫一起被尊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四座文化泰斗也是当之无愧的。
普里什文的美文一旦到手,人们都会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爱不释手。他的美文让人们满怀期待,他的美文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他特意为儿童写的童话故事让成人读了也津津乐道,而他专门为成人写的鸿篇巨制又让少年儿童赞不绝口[5]。
普里什文的作品妙语连珠,余香满口,读着读着就出了神,内心还默默地记诵起来。在普里什文那散发着墨香的书页里,我发现了那么多坦然奔驰的灵魂,那么多有着七情六欲的万物之灵长,那么多活灵活现的动物世界,那么五彩缤纷的植物世界,他们或大声疾呼、仰天长啸,或窃窃低吟、悄声细语,或缠绵悱恻,或欢跃奔腾,或青翠欲滴,都以难以抵御的鲜活与迷人,俘虏着我去猎奇、去琢磨、去咀嚼、去体味。美不胜收的精神大宇宙,在有限的书页里,在他的秘密日记里进行着无限的拓展,最终给人以无穷的欢乐和愉悦,给人以精神的美的享受,给人以情感的高度升华。我真悔恨,三十多年前就得知有一代巨匠普里什文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求真追善慕美的人们,但直到近十几年才能有闲暇一睹他的惊异之美、醇厚之美,相见恨晚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一位作家,普里什文作品的语言生动优美、自然而不做作,还能激发出俄语口语原生态的力量;作为一位从事农学研究的科学家,普里什文让读者既能感受到贯穿其作品中的生态思想、自然哲理,又能学习许多大自然的鲜活知识;作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一百多年前普里什文运用多种摄影手法留下来数千张照片,创作出的作品具有逼真的画面感。普里什文笔下的自然与人类的故事紧密相连、互为主体,延伸了人文的空间,拓展了心灵的世界,让人们明白除了需要关心个人内心世界之外,还需要关注更为广阔的大自然。
在世界文学史上,但凡一部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独特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特定时代文化的烛照。对于地处莫斯科郊外的独宁纳村,我一直梦萦魂牵。当然,我对所有美名传天下、山水甲天下的地方都存着难以遏制的心动。1999年夏末的8月29日,当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郊区独宁纳村[6]这片莫斯科河之滨的美丽富饶的土地时,我便强烈地感到,一曲曲旷世绝唱在普里什文居于斯的此前此后出自他之手乃天经地义之事。再者说来,从1926年开始,普里什文“下意识地听命于自己的爱好,为搜寻有关生长在大自然深处的植物的神话传说,连续几年一直奔波在杜布纳沼泽地附近,一直坚持居住在离沼泽地不远的扎戈尔斯克”(谢尔基耶夫镇)[7]。谢尔基耶夫镇是世人虔诚地称为俄罗斯东正教的“麦加”的圣洁之地。

普里什文故居
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脍炙人口的《金玫瑰》中写道:“我打算在这本书中为我认识的几位最普通的人立传,……他们身后也无从给后人留下哪怕是一丝痕迹。他们整个心灵都为某种热烈的爱好吞没了”[8]。帕乌斯托夫斯基所指的“几位最普通的人”包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契诃夫;有20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守护天使亚·勃洛克;有法国短篇小说的圣手莫泊桑;有俄罗斯乡村生活的歌手布宁;有为时代鼓与呼的高尔基;有开法国浪漫主义之先河的维克多·雨果;有以散文体长诗《红帆》而跻身于那些召唤人们去攀登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的优秀作家之列的亚·格林;有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米·普里什文等著名作家,但普里什文在这些作家中占有特殊位置。帕乌斯托夫斯基强调:“普里什文永远是创造者,是造福于人类的人,是艺术家”[9]。
列米佐夫说:“普里什文是即使饱受沧桑和苦难也未离开俄罗斯的第一位作家”[10]。
帕斯捷尔纳克惊叹道:“我开始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则警句和名言竟然能表达那么多的韵味,几乎真可以赛过一本又一本的大部头书”[11]。
瓦·科日诺夫是一位志存高远的伯乐式文化巨人,他独具慧眼,对普里什文做出了极为深刻而精到的论断:“普里什文是一位艺术家,在他的创作里通过艺术视角关照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实现了极为重要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12]瓦·科日诺夫早在1973年就惊呼:“普里什文的时代已经到来!”[13]1993年科日诺夫又大声疾呼:“如果没有《人间苦难》,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就真是难以想象”[14]。
1948年10月23日,索尔仁尼琴给妻子纳·列舍托夫斯卡娅写道:“你读一下普里什文的《叶芹草》吧,这是一部散文长诗,笔端流淌的是契诃夫和俄罗斯大自然的亲和力。你读过普里什文吗?他是一位文豪呀!《叶芹草》里面很优美地引出了这么一个思想:作为作者,他在自己的生活里之所以做最美好最有益的事情,就因为是爱情失意了,这部长诗是自传体的……读一下,一定读一下吧。要读好的大师,他们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不露痕迹地从内心溜过”[15]。
阿格诺萨夫称普里什文“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16]。
哈利泽夫极为敬仰普里什文和巴赫金。他把他们两位尊称为“20世纪的基捷日人”[17]。哈利泽夫登高一呼,此后便山鸣谷应。
当代俄罗斯作家维·皮耶楚赫在《俄罗斯主题》一书中写道:“顺便说一下,一位有学养的读者,他就是一位触类旁通的生命体,尤其是,他不同于一般读者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独立地做出这样的决断:比方说,……苏维埃时代的第一位天才是普里什文……”[18]
当代学者阿·格里戈良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人》一书中写道:“普里什文在我的这本书里时不时地扑面而来,这也不是偶然的。三十多年前,瓦·科日诺夫说普里什文的时代到来了,但是,这个时代就像巴赫金的时代一样才刚刚到来”[19]。
更耐人寻味的是,正当普里什文包揽文史哲各界鲜亮光环的时候,以诚实和不偏颇见长的农民评论界却对他抛出了自己的微词:“当人们给农民们说,高尔基对普里什文这位作家赞不绝口的时候,一位农民说:‘就让他喜欢他的普里什文吧,而我们喜欢高尔基的书,而不喜欢普里什文’”[20]。
实际上,俄罗斯文学界对普里什文的评价在各个时期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即使是在普里什文逝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研究者在阐释普里什文的时候,对他仍然还是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一些不堪的说法当然也时而有之。就连著名女诗人吉皮乌斯对普里什文也轻率地下了一个“没有人性的作家”[21]的结论。不知是这位天才诗人没有理解普里什文,还是彼此有个人恩怨,抑或迫于什么压力,就草率地给普里什文扣了这么一顶沉甸甸的帽子,她的语言暴力使普里什文长期不甚愉快。乌赫托姆斯基认为,普里什文是一位“只关心别人面貌的作家”。还有部分苏联评论家严厉申斥普里什文“远离活生生的人而逃往别连捷耶沃王国”。文学大师普拉东诺夫在以批评的眼光思考普里什文的《赤裸的春天》时,试图想向人们证实一点:“作者简直是什么人都不需要”[22]。尤里·卡扎科夫在感受普里什文的时候,认为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并断言:“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隐秘的、不愿示人的东西。在我看来,苏联作家中还没有哪位作家如普里什文一样触及这种隐秘的东西”。
那么,在各个时期对普里什文的评价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呢?这就是提出问题并想证明本专著研究的迫切性的重要因由。
事实上,经过好几代读者和评论家的努力,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高尔基、勃洛克、列米佐夫、吉皮乌斯、费多托夫、“拉普”的评论家、乌赫托姆斯基、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帕乌斯托夫斯基、科日诺夫、卡扎科夫、阿格诺萨夫、瓦尔拉莫夫、纳·德瓦尔佐娃、梁赞诺娃、格丽申娜、哈里泽夫、维·皮耶楚赫等,在感受普里什文创作的过程中,人们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一些传统和模式:“没有人性的作家”“只关心别人面貌的作家”;民俗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猎人作家、儿童作家、心理诗人学家;宇宙学家、地球乐观主义者和抒情作家;大自然的歌手和在大自然中摆脱人类社会的作家;在其创作里通过艺术视角关照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实现了极为重要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思想家;在文学进程中跟谁都不像,独辟蹊径、特立独行的作家等。更为严肃的是,这种毁誉参半,有时甚至是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观点和评价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各个时期都络绎不绝地同时出现和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30多年,普里什文一些以前没有出版过的,或出版时有删减的作品完整版相继问世(如《人间苦难》),特别是总量长达18卷的普里什文秘密日记相继出版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位米沙大叔原来还有这么隐秘的、这么鲜为人知的个人世界和艺术宇宙。我们不禁赞叹,这才是一个真实、鲜活、全新的普里什文!只了解其四分之一还不到就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有点为时尚早。
首先必须理解普里什文的原生真实面貌。列夫·奥泽洛夫在《无画框肖像群》一书中给普里什文勾勒了一个可爱的简单轮廓并获得普里什文签名后说:“我一辈子都在读普里什文,就像人们在品尝甘甜的泉水一样”[23]。木雕画家尤利·卡扎科夫极为崇拜普里什文,特意为普里什文精雕细刻了一幅肖像,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普里什文的形象。石印画家尤利·谢里维尔斯托夫的系列石印画和格·加切夫为其撰文创作的文化肖像集把普里什文与普希金、恰达耶夫、勃洛克、彼·弗洛列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等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这让我们惊奇地发现,20世纪的文化泰斗阿列克谢依·洛谢夫、米哈依尔·巴赫金和米哈依尔·普里什文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创作个性又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1990年,费·库兹涅佐夫对普里什文在苏联时期的创作道路做了新的简练的表达:“叛逆后而容忍”。费·库兹涅佐夫写道:“不破坏,不斗争,要肯定自己的真理。只有思考,才能理解,而且理解也是为了评判。不管怎么说,普里什文就像高尔基一样,他‘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强权、杀戮、仇恨甚至丧尽天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现实也无可奈何,所以在20年代末他写道,要‘抗议而不反对现存政权,而只是不满足我的劳动条件’。即使是如此,他还是遇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冲突问题,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个性自由的宣言书’。对普里什文来说,个性自由主题整个一生一直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这样,普里什文对个性自由这个范畴的哲学思考渐渐地就从社会层面转到道德层面。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看到,不可能用‘直接斗争’去消灭恶。等待,让恶自身改弦易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为肯定善而创造,在善中教育人,他认为这就是参与国家的建设生活。他的具体做法是,写着狩猎故事,继续为自己在生活中的权利而斗争,这种权利不是写完就搁置一边,而是写出来给人们看,不是纯属为了赚稿费,而是为了洗涤良心,在写作中寻找唯一的生活意义”[24]。这种表述最明确不过地反映了前几十年文学评论界已成定见的结论:“从现代主义的迷茫到社会现实主义的转变”,我们对这种观点也不能不进行一番再思考。
对普里什文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读者心目中已有的普里什文多面孔形象很明显地反映了他创作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今天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即读者和文艺学家不仅是面对普里什文创作一个接一个的观念变化,而且是在发现一位真实的普里什文的过程中才仅仅开了个头,人们才刚刚开始思考他的创作个性和独特创作风格在俄罗斯文学——从整体上说是在20世纪文化中的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普里什文是一位远远没有被发现的、只有现在才全部回归俄罗斯文学的作家,也只有在最近三十多年才真正确立了“普里什文创作”这一概念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文艺学家研究的对象本身才真正确定。
1993年11月4—5日,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普里什文创作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会上最主要的一点是,介绍了作家独一无二的日记。
在研究普里什文创作的时候要考虑两点:第一,科日诺夫院士等九人编委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筹划于1982年出齐的普里什文8卷全集,就其总量来说比日记要小一些;第二,在细读2017年全部出齐的18卷日记的背景下,即使是普里什文极为著名且广为流传的作品,又获得了新的含义,也就是说,一位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始意义上的真实面貌才渐渐浮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态度对待普里什文的创作?从哪个视角来研究普里什文的创作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必须寻找一个明确的、十分具体的视角来研究普里什文的创作。在本专著中将以作家的主要作品和日记为基础,研究对象是他创作的文体问题,即体裁范畴、语体创新和风格追求。这一学术问题的探讨在俄罗斯已有学者展开论述,但在我国目前还尚不多见,这就是本专著的创新意义。
本专著的实际意义是:叙述文体的基本原理,以创作史实为依据,以体裁分类为原则,以普里什文的主要作品和18卷日记为基础,做出较为中肯贴切的分析和结论,从而推动对普里什文创作的总体研究。
[1] М.Горький.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Том 24.С.264,551 и 552. Го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 1953;См.Писатели о писателя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ртреты.Москва.“Дрофа”,2003.С.133.
[2] 高尔基,转引自利季娅·梁赞诺娃、亚娜·格里申娜编《普里什文个人档案·同时代人回忆录》封四,萌芽出版社2005年版。
[3] 米·普里什文:《大地的眼睛》,潘安荣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4]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5] 中国多种中小学教材及课外阅读书籍中收入了普里什文的多篇作品。他时而作为民间故事的写作者与克雷洛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并列齐名,时而又作为描写俄罗斯自然的圣手与普希金、屠格涅夫、费特等同时出现,他还作为著名的儿童作家和马克·吐温、罗大里等并列。普里什文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20世纪之初,他是作为怀有强烈宇宙感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步入俄罗斯文坛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虽历经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衰落、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盛,却始终保持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不仅拓宽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主题范围,而且为其奠定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参见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六年级(下册),马新国、郑国民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6] 独宁纳村是普里什文故居博物馆所在地。潘安荣老师译为杜尼诺。作者注。
[7] 米·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潘安荣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8]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9]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10] 利季娅·梁赞诺娃、亚娜·格里申娜编:《普里什文个人档案·同时代人回忆录》,萌芽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1] 利季娅·梁赞诺娃、亚娜·格里申娜编:《普里什文个人档案·同时代人回忆录》封四,萌芽出版社2005年版。
[12] 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1.С.337.
[13] 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1.С.342.
[14] Вадим Кожинов.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1.С.681.
[15] Журнал《Человек》,1990.No 2.С.151.
[16] В.Агеносов.Совет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оман.М.Изд-во“Прометей”МГПИ им.Ленина,1989.С.103.
[17] В.Е.Хализев.Опыт преодоления утопизма//Постсимволизм как яв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1995.С.12-17.Цит.по:Н.Дворцовой. 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писатель.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туры,2004.No 1.С.65.
[18] Вячеслав Пьецух.《Русская тема》.Москва《Глобулус》,2008.С.3.省略号是笔者所加。
[19] Армен Григорян.《Первый,вторóй и трéтий человек》,—М.: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4.С.21.
[20] Цит.по:журналу《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ýры》,2015.№.4.С.359.
[21] 吉皮乌斯在《文学家与文学》一文中认为普里什文的创作“用眼睛代替心灵”,“缺乏人性”,参见米·普里什文《我的随笔》,杨素梅译,收录在潘安荣译《大自然的日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См.М.Пришв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Том 3.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3.С.8.
[22] 普拉东诺夫此说后来引起了很大争议。
[23] 列夫·奥泽洛夫:《无画框肖像群》,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和“РАНДЕВУ-АМ”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4] Журнал《Наше наследие》,1990.No 2.С.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