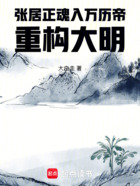
第2章 早朝争锋
自万历元年,张居正改革早朝时间。
逢三、六、九日上朝,每月上朝九次,这是为了给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以充足的学习时间。
而今日正是万历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京中四品以上官员,并六品以上都察院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及六科给事中,近千人汇聚在午门外等候。
卯时方至,钟鼓齐鸣。
一列文官由左掖门进,武官则由右掖门入。
朝中文武众官员浩浩荡荡过金水桥后,按品级于御道两旁分列。
一行龙撵在众侍卫护送下,来到门廊内的金台旁。
朱翊钧下了龙撵,由一小太监领着到了金台上登座。
此时,骤雨已去,天空放晴,旭日初露。
晨光压住了夜色的静谧,升起了白日的喧嚣。
等鸿胪寺唱罢鸣鞭,露天广场上的百官开始齐齐跪地拜叩。
朱翊钧端坐龙椅之上,第一次以这个角度俯视下方三拜九叩的百官。
再一次感受到了皇权的冲击,是如此的猛烈。
他扫视一圈场中百官,微微抬手,“免礼。”
众官员谢恩起身。
张四维横跨出一步,躬身行了一礼,“陛下,张居正已于六月二十日在家中离世,臣等悲恸……”
张四维语出哽咽,渐渐泣不成声。
他刚升任首辅,依照礼法,也应该对上一任的逝去而表现出悲痛欲绝的神态。
否则如何彰显大德?
张四维的哭泣声,渐渐带动着广场上所有朝臣也哀叹不止。
百官皆是袖掩面,泣声起,呜咽之声此起彼伏,似是进到某处灵堂之中。
朱翊钧静静看着场中所有人如此卖力,且声情并茂的表演,心中毫无波澜。
这种表演他自己曾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见过多次,也带头参与过多次。
当时,他也是其中一员,也是在这广场之中,也是掩面而泣,悲痛欲绝。
而当时心中所想,想必也和此时场中人一样,喜悦之情占了大半。
要说喜极而泣,也不为过。
朱翊钧起身,看向东面正冉冉升起的旭日,像模像样地仰天长叹,悲戚呼道:“先生……
朕以幼冲嗣位,赖先生匡弼启沃,四方治安,九边宁靖,祖宗列圣,亦鉴知先生之功。今先生捐馆,朕痛彻肺腑,特诏追念其功,以彰忠烈。”
张四维更是上前一步,“陛下圣明,定要厚葬张大人,以彰国之恩典。”
朱翊钧又连连惋惜数声,看向张四维叹道:“爱卿所言极是,依卿之意,该当如何?”
张四维挺直腰杆,转身巡视身后一众官员,作深思熟虑状。
片刻之后,面对龙椅恭敬作揖,“依微臣所见,当今天下安定,国祚昌隆,皆因自圣上御极以来,宵旰忧勤,励精图治,上法唐虞三代之隆,下轶汉唐宋元之轨……”
朱翊钧坐回龙椅,耳中充斥着张四维那华丽无比的辞藻,时而点头示意,时而蹙眉凝思,一副仔细聆听老师上课的好学生模样。
而实际上,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心思全在其他官员身上。
朱翊钧首先注意到的是兵部尚书梁梦龙、吏部尚书王国光、工部尚书曾省吾。
这三位尚书全都是微微低垂着头,脸色铁青,满面悲愤中带着一抹黯然神色。
三人作为张居正的门生,亦是死忠,也深知自身靠山不在,大势将去,被朝中言官参劾,最终致仕只是时间问题。
朱翊钧将这一切收入眼中,稍感欣慰。
他之前搭建起来的政治班底,目前来看还未全军覆没。
但,也就仅剩这三人而已。
其他人或是倒戈,心甘情愿拜到张四维门下。
或是摇摆观望,待时局大定之后再作决定。
此时,张四维已经吐沫横飞地说了半天,嘴角溢满白沫,终于还是说到了正题上。
“皇上,可予张大人一子,尚宝司丞之职,以示对其子孙照顾,彰显皇上恩泽。”
“张爱卿所言甚是,准了!”
朱翊钧点点头,巡视一圈场中百官,“张先生为国尽忠,怎能以薄礼相待?朕深念张先生功绩,特赠上柱国,赐谥文忠,祭十六坛,予一子尚宝司丞一职,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厚葬。”
“圣上洪恩……”
百官齐齐伏地跪拜,齐声高呼。
朱翊钧扫了申时行一眼,“申阁老拟旨,宣发各处。”
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再次叩首领旨,“臣遵命。”
经此一番,张居正在朝堂上算是寿终正寝,成为过往。
高楼坍塌,碎石一地,必有后人聚石再建,百官亦是心照不宣。
“臣有本奏!”御史雷士帧出列大声上奏。
朱翊钧看向身为言官的雷士帧,“何事?”
御史雷士帧道:“禀圣上,前礼部尚书潘晟久玷清华,不闻亮杰,且秽迹昭著,曾受先帝斥责,若是让他复官,不单损朝廷颜面,更有蒙蔽圣上之嫌。
那潘晟之恶名于朝堂百官中人尽皆知,还请圣上下旨喝令回籍,永不录用。”
朱翊钧站起身,盯着御史雷士帧良久,冷声道:“朕深知潘晟此人为官清廉,怀有仁心。
至于他曾受先帝斥责,亦是勇于觐见所致,此事从先帝遗诏中可见,并非方才卿之所言,难道爱卿要质疑先帝遗诏?”
之前内阁当中,申时行虽才能过人,但行事风格过于中庸。
而那张四维徒于察言观色,治世之能寥寥。若是处理朝堂中事,还算过得去,但让他继续大力推进变革,那便不堪重用。
张居正并不放心将这十年的变革成果交予内阁众人。
无奈只能在临终前上书皇帝,起复潘晟。做到有备无患,期望能将生前的变革继续延续下去。
在张居正眼中,惟潘晟最是推崇变革,且为官清廉,更有济世之心。
他在老家绍兴曾多次开仓放粮,周济难民。
更是将自家近百余亩良田变卖,筹得资金捐入县学之中。
在当地名声甚隆。
此时的潘晟,大抵在赴京途中。
雷士帧见皇上几句话就把潘晟的问题,与先帝遗诏牵扯在一起,赶忙惶恐道:“臣不敢!”
这时,一旁的御史魏允贞见事不妙,急忙出手相助,誓要把潘晟的德行问题,重新再拉回来。
他领五名御史同时跪地,“圣上身居宫中,忙于治政,对于远在绍兴的潘晟知之不深,方才雷大人上奏所言,并非谬言,还请圣上三思。”
“请皇上三思……”
几乎同时,五名跪地的御史,齐声附和。
居于首位的张四维见此情形,嘴角微扬,转身赞许的扫了一眼那跪地的几位言官。
在他看来,当今天子年纪尚轻,面对言官联名上奏,根本毫无招架之力,更何况只是为了一个在朝中毫无资源的潘晟。
只要潘晟复官不成,随后再除冯保,张居正所有的重要余党就全部清除。
至于吏、兵、工三位尚书,在张四维眼中,不堪一击。
更何况这三位尚书,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不敢有任何作为。
张四维慢悠悠的上前一步,躬身奏道:“圣上,若是一人弹劾潘晟许是有失偏颇,可如今众御史一同上书,所言皆直指潘晟,想是那潘晟必是有不足之处。
圣上,朝堂用人,需得谨慎,臣还请皇上慎重,切勿让那等小人蒙蔽。”
朱翊钧听着,微微颔首。
假如潘晟被参倒,那日后内阁之中,就再也没有能制衡张四维的阁员。
放任张四维在内阁中一手遮天,当下摇摆不定的言官们为了自己的官帽,也会一边倒的投到张四维麾下。
介时他一手掌控内阁,一手掌控言路,废除改革只是时间问题,更有可能会牵扯到张家一众老小。
朱翊钧对朝中百官了解甚深,更何况这位由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张四维。
他们的那点儿小心思哪能看不出?
当下硬碰硬并非良策,唯用拖字一诀,先让潘晟顺利入京,以谋后定。
朱翊钧思忖再三,悠悠道:“众爱卿也是身居京城,并未去往那绍兴当地走访查看,大概也是听人所言。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何不等那潘晟入京后,再议此事?
况且之前已有人回报给朕,细细说明潘晟为人,乃是德行俱佳,可堪大任之臣,众卿……私人恩怨勿要掺入朝堂!”
朱翊钧的一句“私人恩怨勿要掺入朝堂!”便给这帮御史言官定了性。
张四维满脸惊讶,疑惑地看向金台之上年纪轻轻的大明天子。
这位天子面上虽还带着稚嫩,但言语之间却是稳重,且太极之术极其老练,丝毫不见这年龄该有的青涩。
众言官同样面面相觑,刚要继续上奏,就见张四维袖中的手伸出一半,勾了勾小拇指。
众人便叩首起身,站回之前位置。
这时,已经得到张四维授意的御史江东之出列,躬身道:“皇上,臣亦有本奏。”
朱翊钧看向江东之,点点头。
江东之长吸了口气,言道:“臣参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欺君祸国,贪赃枉法,重用逃犯,并将逃犯徐爵升任锦衣卫同知。
此等要职竟由逃犯担任,大明律法何在?天子安危何在?冯保这阉宦心中无主,其心可诛,理应处死。”
“当朝竟有这等事?爱卿所言可有实据?”朱翊钧故作震惊,双目圆睁。
御史江东之瞥见龙颜大怒,心中窃喜,忙道:“陛下,徐爵确系逃犯,事实已经查明,人证物证俱在,望陛下明鉴。”
朱翊钧默默感叹,冯保啊,冯保,与当朝这帮文官斗,焉能不小心谨慎?竟让人抓到这样的把柄。
那徐爵并非生人,乃内廷与外廷的联络人。
此人言行油滑,品性贪婪。
身为逃犯却不知低调收敛,更是嚣张对人,任意勒索来京官员,其劣迹种种早就在京城中传开。
之前,张居正便知这人早晚要出事,只是一直忙于整治内阁和百官,无暇顾及。
期间,张居正也不止一次旁敲侧击的提醒过冯保。
谁知那冯保仗着有内宫这座靠山,竟然充耳不闻,完全不当回事。
朱翊钧虽对徐爵没有任何袒护之心,但这人牵扯冯保。
而冯保此时是改革一派的最后一层堡垒。
朱翊钧权衡之后,对江东之慨然道:“冯保伴朕多年,未见其心有异,然爱卿手握实证,朕岂能不信?朕深感痛心……”
顿了顿,又道:“那就让冯保来见朕,朕要当面问清此事,朕倒要看看冯保在爱卿实证面前,该如何解释。”
江东之伏躬身道:“陛下圣明!”
朱翊钧扭头对身旁的小太监吩咐道:“着冯……着大伴见朕。”
小太监稍稍一怔,立即回道:“奴才遵命。”说罢便快步绕廊出去。
方才参奏潘晟的近十名御史言官,这时也忙跪地,大声道“陛下,冯保掌控东厂、锦衣卫,权势滔天,潘晟的那些美名许是冯保伪造,以来蒙蔽圣上。
冯保为何会为潘晟美言?必是他们之间有银钱勾当,那潘晟的清廉名声,也不可信,还请陛下明鉴。”
朱翊钧点头道:“众爱卿一心为国,朕颇感欣慰,一切等冯保来了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