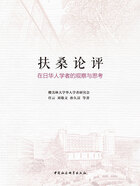
一 20年的长期萧条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原因探析
(一)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和失去的20年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可谓是起伏跌宕。如图1所示,从50年代中期起,日本经济在经历了约10年的重建恢复后步入了辉煌的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1%,堪称世界奇迹。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战后出现了首次负增长,但很快从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维持了平稳增长的状态,到1990年平均增长率为4.2%,高于同期美、德等先进国家的水平,也可谓是一枝独秀。但是,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1991—2012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纵观而言,日本经济增长经历了两次放缓:从高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衰退,如同下跌了三个台阶。

图1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率(财政年度,%)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SNA数据制作。
过去的20余年,日本经济萧条期之长,问题之严重,实属罕见:(1)实际GDP增长率有五次为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仅有0.9%;1992年名义GDP为487.96万亿日元,而2012年反而只有475.57万亿日元,经济总量及人均量在世界排名中均下滑。(2)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从1997年度的467万日元降至2009年的最低点406万日元,2011年度也只有409万日元(图2)。(3)消费者物价在1998—2005年、2009—2012年期间两次持续下降,而反映物价总水平的GDP减缩指数从1994年最高的110.96点开始几乎连年下降,2012年降至91.57(2005年为100),这样长的通货紧缩在战后发达国家里没有先例。(4)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逐年迅速增加。2013年政府各类债务余额高达1097万亿日元,为GDP的2.28倍,远超过第2高位的意大利(1.296倍),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里最为糟糕(图3)。总之,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凋零,人民普遍感到前途迷茫、信心低落,所以日本国内称之为“失去的20年”。[2]以下,我们首先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失去的20年”的原因。

图2 日本工薪阶层平均年收入(万日元)
资料来源:国税厅平成24年民间给与实态统计调查并根据财务省网站资料制作。

图3 政府债务余额各国比较(对GDP,%)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网站资料制作。
(二)长期萧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我们首先从需求角度分析。从大的走势来看,正如吉川洋指出的那样,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人口大迁徙以及家庭户数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民间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的增长,并形成了“投资唤起投资”的良性循环,整个经济增长势头自然十分强劲。此后经济增速的放缓,正是由于上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3]
表1说明,199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里,占总需求比达六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速虽然略高于GDP平均增长率,但较前期大幅度放缓,而占总需求约三成的总资本形成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991—2000年竟为负1.46%,此后的2001—2012年也是负1.41%,这显著拉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另从储蓄角度来看,泡沫经济崩溃后虽然个人储蓄部分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一直在下降,但企业储蓄,特别是大企业储蓄部分却大幅度扩大,导致民间储蓄净盈余一直维持在高位或增加。[4]总之,投资的严重不足造成了需求长期不足的局面。
表1 日本总需求项目各期间简单平均增长率(%)

消费低迷特别是民间投资长期不足的原因,在90年代可主要归结于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泡沫经济的崩溃产生了严重的负资产效应,抑制了民间消费;(2)负资产效应也大大损伤了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一方面大量不良债权导致银行金融功能低下,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引发了数年的信贷萎缩,另一方面企业也在泡沫崩溃后忙于清理债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5](3)90年代政府在清理不良债权及应对金融危机时反应滞后,对应不足;(4)还有不少学者,如岩田野口及冈田等认为日本银行采取的金融政策屡屡失误,既是泡沫经济产生和加重的原因,也是泡沫崩溃后长期萧条的罪魁祸首。[6]至于最近十多年的消费及投资低迷,则主要归咎于长期的通货紧缩及黯淡的经济前景所导致的国民及产业界对未来严重丧失了信心(2007)[7]。
另一方面重视供给的学派,如Hayashi and Prescott[8]认为需求不足不能很好地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而90年代日本的人均劳动时间减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9]的下降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他们计算得出日本劳动力人均GNP增长率从1960—1970年的7.7%下降到1991—2000年的0.5%,同期TFP增长率从4.91%下降为0.191%,据此认为并不是需求小于潜在增长率,而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身大幅下降了。换言之,由于劳动投入率出现负增长和TFP增长率下降,导致原有的增长路径大幅度下移,这才是日本经济增长低迷的原因。林文夫进一步拓展了上述2002年的研究,在考虑IT产业带来的价格变化等影响后重新推算了TFP,得出了与原研究类似的结论。[10]
我们也可根据日本JIP数据库(2013)的经济增长统计来印证上述结论。如图4所示,1990年代以来劳动力数量投入增长率一直为负,资本投入增长率也从20世纪70、80年代的接近2%降到90年代的1%,21世纪头五年更只有0.42%,后五年则为0.06%,这些数据均表明了日本经济的要素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TFP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五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1%、1.99%、0.98%、1.79%。而整个1990年代的TFP平均增幅低于0.2%,进入21世纪后除2000—2005年达到1.07%外,2005—2010年又归于零,可见总体而言TFP增幅也大幅度下降。

图4 各期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JIP数据库(2013年)(宏观及附加价值口径)数据制作。
笔者认为从问题的复杂性来看,日本经济萧条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割裂需求与供给来片面解释。但从问题的长期性来看,有必要多从供给方寻找原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萧条,主要是因为资本投入增速放缓和劳动投入减少,以及TFP增速放缓所造成的。这其中要素投入的变化较容易解释,比如资本投入增速放缓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减少,而劳动力投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低出生率及人口老龄化,以及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缩短工时的影响。但为什么TFP增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这个问题关乎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在下一小节重点论述。
(三)生产率增幅放缓原因的进一步解析
首先,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进一步确认日本经济生产率增幅放缓的事实。笔者根据JIP数据库2012年数据计算得出,日本的制造业TFP在1990年代初期便结束了较高的增长,2009年的制造业生产率与1970年相比只提高了2.39倍,而若按1970年到1991年的增速,应可提高至4.12倍。另一方面,非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则一直没有显著增长,2009年仅为1970年的1.17倍(图5)。2005年日本多数非制造业领域的TFP水平只有美国以及欧盟15国(除希腊外)的一半。另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代初曾一度达到美国的近80%,而2010年只有美国的67%左右,且低于英、法、德、意等国。[11]
关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幅大幅度放缓的原因近年已有了诸多分析。深尾京司[12]在其研究团队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全面总结。

图5 制造业与非制造业TFP变化(1970=1)
资料来源:根据JIP数据库2012年制作。
首先,从投入的角度来看,深尾(第2章)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日本的信息通信产业(ICT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幅度在1995年后尽管低于美国、韩国,但仍超过5%。不过ICT投入产业,比如商业及运输等流通业及除电子机械产业以外的制造业从1995年起TF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这些产业里ICT投资大幅度不足。1995年以来商业、运输、金融、对单位及对个人服务业等非制造部门的GDP增长中,ICT的贡献率在发达七国中处于最低或倒数第二位。研究还发现,日本企业尽管在研发方面投入较多,但是在强化企业竞争力的投资方面,如在企业结构和组织改革,以及员工的脱岗培训上投入非常之少;加之近年来非正规雇佣的比重逐渐上升,而非正规人员难以得到充分的企业内在岗培训,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素质,这也是拉低TFP增幅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产业新陈代谢的角度来看,深尾(第3章)将制造业TFP上升的因素分解为内部效果(企业内部削减成本、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等所产生的效果)、再配置效果(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或工厂扩大规模,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缩小规模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果)、进入效果(TFP较高的企业或工厂的新设及进入效果),以及退出效果(TFP较低的企业或工厂关闭及退出所产生的效果)。通过对这四项效果的分析,他们发现199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的内部效果增速降低,二是企业退出效应为负值,此外进入效果的增幅也处于停滞状态(图6)。

图6 制造业TFP上升率的要素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深尾京司(2012年)第154页数据制作。
内部效果增幅下降,表明日本企业通过内部经营合理化等努力来提高效率的改善越来越难以奏效;退出效果为负值,说明长期以来生产率很低而应该淘汰的企业没有退出,但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却通过向海外转移加速了退出;此外,进入效果贡献为正,说明新设立并进入市场的企业或工厂总体而言生产率水平较高,不过这项效果在90年代后不如80年代贡献大,表明新企业的增设趋势不够活跃。
与美英韩等国的比较,可以进一步发现日本企业TFP增长中内部效果贡献相对较大,而再配置以及进入效果贡献小,特别是退出效果一贯为负。英美等国在经济环境较差时主要是靠缩小、关闭生产率较低的工厂,通过再配置及进入退出效果来提高生产率的。而在日本,尽管1990年代以来生产率较低的小企业遭到淘汰的较多,但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纷纷将工厂迁到海外,导致加重平均计算所得出的退出效果为负值。研究表明特别是电子零部件、通信器械、计算机等向海外转移的产业带来了大幅度的退出负效果。[13]
对非制造业的分析也表明,近十多年里大部分非制造业出现了较大的再配置负效果,特别是建筑及运输业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的人员削减量显著,对整个非制造业的生产率下降有较大影响。同时,电力、煤气、供水、广电等服务行业的新陈代谢能力极低。[14]
此外,深尾等人对大企业及小企业分类研究,发现大企业及大工厂的TFP在1990年代以后仍然是上升的,但中小企业TFP增长率出现了停滞,在制造业及非制造业领域里,均出现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TFP差距扩大的现象。研究表明,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额比较高的企业,以及出口占比及海外投资占比较高的企业其TFP增长率一般较高,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则在研发及国际化方面均处于落后状态。当然,大企业向海外转移也削弱了其与国内供应链企业特别是中小零部件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合作关系。大企业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减少,也可能是中小企业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
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西村、Nishimura,Nakajima和Kiyota认为,日本企业的自然淘汰机制本身就不够活跃,从1997年起更是出现了生产率低的企业生存率高,生产率高的企业反倒淘汰率高的反常现象。Hayashi和Prescott也认为,生产率增幅高的企业走出国门,而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企业留在国内,且没有被淘汰,所以全体的生产率增幅必然会下降。Kimura和Kiyota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出口型企业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要比只限于国内的企业高。宫川努详细分析了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性的增幅,认为在整个90年代全部产业的TFP增长率比80年代均有下降,其中一半产业还为负增长,但是各产业的TFP增长率与本产业就业人口数的变化基本没有相关,表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资金以及劳动市场的流动性也大大降低。对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的原因的分解分析表明,除TFP上升率下降外,劳动力的再配置效果在90年代为负效果。细野则从金融角度分析了日本生产率的变化,他认为金融危机导致了金融中介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了新设企业以及生产率水平较高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扭曲了资金分配,从而拉低了生产率增长水平。[15]
综上所述,企业新陈代谢能力低,生产要素配置缺乏效率及流动性,是导致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生产率低迷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为什么新陈代谢如此困难?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日本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等更微观的层次上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