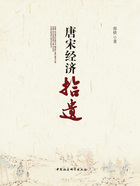
(一)诸子平均析产方式的形成过程
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在我国历史上并非自私有制形成伊始即已有之,是到战国时期才逐步形成的。
在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下,贵族爵位是权力与财产的综合载体,由于权力不能分割,所以世袭的时候只能采取整体性传继方式,由诸子中的一个人继承,其他的儿子无份。[1]有关论著所说的这个时期的长子继承或幼子继承制,主要是就天子的王位和贵族的爵位传继而言的,财产的继承只是其中的附属内容。事理明确,毋庸赘言。只需补充一点,商朝王位继承中曾经有过“兄终弟及”方式,这种方式的潜在前提,是所有的儿子对父王的王位有同等的继承权,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长子继承和幼子继承并存;换句话说,这中间已经蕴含着诸子平均(平等)继承的因素。
相对于贵族而言,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庶人没有爵位,能够传给子孙的只是财产。单纯的财产可以任意分割,不一定非要采取由一个人继承的整体性传继方式。不过,商周时期地广人稀,有了劳动力才能开垦土地,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尚处于次要地位,土地所有权的事实和观念还不充分;[2]特别是平民庶人仍然处在宗法制度的笼罩之中,个体小家庭虽然已经存在,却不具备独立性,形成小家庭家产继承方式的前提尚不成熟。至于《礼记·坊记·丧服传》上说的“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以及“昆弟之义无分”等主要是一种说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
当然,不是说当时的平民庶人家庭中不存在继承方式。李亚农先生根据甲骨卜辞中商王武丁的儿子和妻妾都有自有土地的记载推论说:“析财异居,这是殷人普遍实行的制度,而且实行得非常彻底。”后来又进一步讲,商周时期不仅王室贵族,而且在“庶民的宗法中,长房、二房、三房、四房等继承财产的权力大致相同,地位也大致相等”[3]。说得很肯定,可惜没做具体论证。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极为缺乏,没有明确直接的记载来说明当时的分家析产状况,有关论著只能采用间接方式,从当时的家庭规模和结构来推论分家情况。根据考古发掘的商周遗址的居室结构来看,有单间、双间和多间三种,比如商代,双间和单间结构的占80%以上,[4]说明当时的家庭多为一夫一妻制小家庭,间或有父子两代及兄弟同居的扩展型小家庭。由此推论,既然不再以父母兄弟同室而居的大家庭为主了,那么,家产就可能不是整体性传继,因为小家庭的组成是以父家庭的不断分异即诸子析产方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也与李亚农先生所述相吻合。
比较明显的是,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松弛,个体小家庭的独立性明显增大了。《管子》的《问篇》中有“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一条,虽然还是与“宗子”即大宗对称为“余子”即小宗,实际上已经是就小家庭的诸子析居而言了,所以刘向解释说“出离,谓父母在分居也”。分居,应当以析产相伴随。孔子认为大禹之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不如以前了,所以主张用礼义教化“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所讲的也主要是个体小家庭内部的事情。[5]有学者根据《左传》中的史实推论说,到春秋后期的襄公、昭公和哀公时期,贵族家庭以兄弟同居为主,有“从兄弟”的较少,有“再从兄弟”的更为罕见,庶民阶层也以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为主了。[6]大家庭演变为小家庭已经成了一种发展趋势。
进入战国以后,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孟子为地处鲁南的滕国规划的著名的井田制度中,以“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为理想愿景,所反映的乡村组织已经不是宗族,而是乡、井等行政编制了,所以不说同姓和睦,而说“百姓”和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7],乡井之下是家,每家有田百亩(休耕田,相当于可耕田33至50亩,折合为今制约为可耕田9亩至15亩),正是粗放耕作时代个体小家庭的经济基础。孟子为梁惠王设计的家庭职能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如果家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8]。几乎同时的李悝说魏国的家庭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9]……都证明当时的“家”已经是以一对壮年夫妇为中心的三代小家庭,不是父子兄弟同居的大家庭了。这主要是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情形。
商鞅初入秦时,秦人因与西戎杂处,比山东地区落后,仍然处在“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阶段。[10]商鞅是卫国人,他把秦国的这种习俗看作“陋习”,是与他所生活过的卫国的习俗相比较而言的,表明当时卫国所在的中原一带(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再通行父子兄弟同居,已经是与山东地区相似的直系血缘关系小家庭了。
商鞅为了增强秦国在争霸中的实力,扩充农业人手和士兵的来源,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动用行政力量强行拆散了这些父子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如鲁、卫矣”,推行与山东、中原一样的以一对夫妇为主的小家庭模式。[11]为此,商鞅在变法中采取了三个相互配套的具体措施:一是直接取缔父子兄弟同居的大家庭,第一次颁布变法令的时候就明确规定,“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改变同居陋习,“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并辅之以经济制裁手段,“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2],迫使秦人改变了落后的生活起居方式,每家只能有一个壮年男子,儿子成年或结婚后就要另立户头。二是实行统一的户籍法,使“四海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3],新组成的个体小家庭获得了在官府版籍上独立户头的资格,成为官府的编户,从而脱离了宗法制度的束缚。三是实行“连坐相纠”之法,让民户每五户或十户相互监督,纠告不合法令的家庭组织形式,用法律手段稳定住了新建立的个体小家庭。
在前后几次的变法令中,商鞅都没有规定专门的家产析分方式的条文。但是,强令分居即建立个体小家庭,其间已经包含了析产的内容和具体方式。因为其一,儿子与父母分居、另立户头的时候必然带走一份家产,有几个儿子陆续带走几份家产,等于把家产由一个父家庭所有变成了若干个子家庭所有,由整体传用变成了析分继承,这便客观地促进了诸子析产方式的形成。其二,每个儿子单立户头之后都要生产、生活、纳税、服役,负担相同,加之血缘关系相同,所以从父家庭中分出去的财产也应该大致相同,这便在诸子析产中加进了“平均”因素,形成了所谓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
在大量的平民庶人从宗法制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变为户头独立的个体小农的同时,商鞅在变法中还废除了世卿世禄的制度,使贵族阶层的权力与财产趋于分离。多数贵族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只剩下了财产,在传给子孙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可了。这样,除天子的王位和少数贵族的爵位继续由一个人(长子或其他儿子)继承外,贵族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也渐渐地与平民庶人一样——由诸子平均析分了。
由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在秦国,商鞅是在以增加耕战人手为目的的变法过程中强制推行了个体小家庭,从而催生了家产继承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并且通过废除分封制度,使贵族阶层的家产传继方式与之趋同了。直到后来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这套制度,依靠的仍然是行政力量。不过,商鞅的这些做法非但没有违背、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随着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宗法制大家庭必然解体,让位于个体小家庭。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临界点,如前所述,商鞅变法前后在山东和中原的广大地区已经自发地出现了由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的趋势。商鞅在秦国变法中推行的制度与这个转变趋势是一致的,只是由于秦国在当时相对落后,商鞅利用行政手段猛推了一掌。秦统一以后历代都沿用了商鞅的办法,并且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分家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