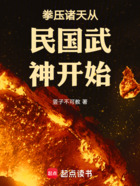
第39章 釜底抽薪
在自家“富记胶行”胶坊门口,孙福贵蹲在那儿,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墙角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阿胶,唉声叹气。
深褐色的胶块上结着一层白碱,在秋日的阳光里泛着冷飕飕的光,再瞧瞧对街“百草胶坊”,阵阵甜香飘来,这鲜明的对比,可太扎眼了。孙福贵猛地砸了下旱烟袋,嘴里骂骂咧咧道:
“好你个白景隆,把胶熬得跟蜜饯似的,就会哄骗那些妇孺,简直坏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太狠了!”
“简直是釜底抽薪!”
“阿胶糕卖的那么便宜!”
“这是赶尽杀绝,不给我们留活路!”
可骂归骂,库房里那八百斤老胶,都堆了足足三个月了。之前赊账的店铺,早都断了往来,如今连给婆娘抓药的钱,都得抠抠搜搜地省着。
更要命的是,镇上的百姓都跟被勾了魂似的,一股脑儿往百草胶坊跑,嘴里还念叨着:“人家新出的阿胶糕,甜滋滋的,三钱银子就能买半斤,比老胶可强太多了。”
此刻,在百草胶坊的后院里,白景隆正忙着往木模里浇筑新熬好的阿胶糕。那琥珀色的胶体,裹着饱满的核桃仁和红枣,这香甜的味儿,直把一旁的学徒们馋得直咽口水。白景隆擦了把额头的汗,转头对姐姐白玉芬说道:
“姐,把那些试吃匣子分给走街串巷的货郎们,跟他们说‘百草阿胶糕,一文钱就能尝鲜,能补气血、养身子,不管是妇人还是小孩,都爱吃’。”
白玉芬瞧着案几上码得整整齐齐的糕块,嘴上嫌弃地说:
“你这哪像是在做药啊,倒像是开了家点心铺子。”
可话虽这么说,她还是亲自监督伙计们,用桑皮纸把阿胶糕仔细包装起来,纸上还印着烫金的小字:“百草秘制阿胶糕,药食同源,老少咸宜”。
三天后的早市,百草胶坊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白景隆手持长刀,熟练地切着糕,刀刃过处,里面饱满的果肉露了出来,他笑着招呼道:
“大爷,您尝尝这块,这里面用的是山东的金丝小枣、太行的薄皮核桃,可都是顶好的料子。熬胶的时候,还加了蜂蜜和黄酒,一点腥气都没有。”
卖豆腐的王老汉咬了一口,砸吧砸吧嘴,称赞道:
“嘿,还真没那股子驴皮的臭味!给我称二两,拿回去给我家婆娘补补身子。”
王老汉话音刚落,人群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喝:
“好啊,竟敢混淆药食!阿胶那可是滋补的上品,怎能容你这般糟践?”
众人纷纷回头,只见老胶坊“老周记”的周师傅,手里攥着一块胶块,从人群里挤了进来。他身上的青布衫,还沾着熬胶留下的碱渍。周师傅手指着案板上的阿胶糕,声音都气得发颤了:
“白景隆,你拿这糖水似的东西糊弄百姓,你可知道,老胶得经过九蒸九晒,那得多花时间、多费力气啊?你这么搞,是要断了我们这些匠人的活路啊!”
白景隆不慌不忙,慢悠悠地擦着刀,说道:
“周师傅,您熬了四十年的胶,肯定清楚老胶性子燥,脾胃虚弱的人吃了,不但补不了,还得遭罪。我这阿胶糕,加了健脾的红枣、润肺的桑葚,性子平和,味道甘甜,就连八岁的孩童都能放心吃——”
说到这儿,他忽然压低了声音,“况且,如今达官贵人都只认咱家的九朝贡胶,您再瞧瞧您库房里的老胶,要是再卖不出去,怕是得烂在缸里了吧?”
周师傅的手停在半空中,脑海里浮现出昨夜儿子蹲在灶台前,就着咸菜喝白粥的模样。原本想着留着老胶,等涨价了再卖,可如今,连灶里烧的柴火,都得去赊欠了。
白景隆瞅准时机,赶忙递上早就准备好的契约,说道:
“您的胶坊,我全盘接手,以后还挂着‘老周记’的字号。您呢,就做我们这儿的首席师傅,每月二十两俸银,可比您一个人单打独斗强太多了。往后,我还要开办胶坊学堂,让您的手艺传遍四方。”
周师傅盯着契约上鲜红的手印,粗糙的拇指来回摩挲着“首席师傅”这四个字,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长叹一声:
“罢了!不过,你得答应我,熬贡胶的时候,还得用桑木火、阿井水,可不能坏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
收服了周师傅后,白景隆又把目光投向了财大气粗的郑大钱。
这会儿,郑大钱的“兴隆号”胶坊正大门紧闭。郑大钱躺在太师椅上,听着账房先生汇报亏空的情况:
“东家,这个月又赔进去五十两了。库房里的胶要是再卖不出去,可就全砸在手里了。”
正说着,小厮匆匆跑进来通报:
“东家,白府少东家求见。”
郑大钱一听,赶忙整了整身上的马褂,堆起满脸的笑容,出门迎接。白景隆一进门,就递上一个精致的锦盒,里面装着一块晶莹剔透的九朝贡胶,说道:
“郑老板,您知道布政使夫人前段时间,为啥订了二十斤这种胶吗?”
郑大钱盯着那块贡胶,喉咙动了动,敷衍道:
“不就是成色好看点嘛。”
“您说错了。”
白景隆摇了摇头,解释道,“贵人要的是体面,百姓要的是实惠。您要是跟着我干,上等胶就走贡胶的路子,普通的胶就做成阿胶糕。到时候,我按股份给您分红——”
说着,他展开一张济南府胶坊分布图,“等咱们占了济南的市场,下一步就往兖州、青州铺货,甚至还能进京,把货呈给宫里,您就等着坐收红利吧。”
郑大钱心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琢磨着,自己再这么硬撑下去,不过是赔本赚吆喝;可要是加入百草胶坊,既能把库存清理掉,还能拿股份分红。他捻着胡子,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我要占一成干股。”
白玉芬在一旁冷笑一声,递过去另一张契约,说道:
“郑老板,您库房里的胶,都搁了三个月了。要是再拖下去,恐怕连当柴烧都没人要。现在入股,您还能拿半成。要是过了三天嘛……”
她指尖轻轻划过契约上“半价收胶”的条款,“可就由不得您选了。”
郑大钱盯着条款,肥嘟嘟的脸涨得通红。他想起前几日布政使夫人派人来退单时那冷冰冰的模样,又想起同行们私下里都在说“跟着白景隆才有活路”,终于一咬牙,说道:
“签!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账目可得清清楚楚的。”
霜降后的第二天,泷河镇的胶坊都齐刷刷地换上了新匾。
老周师傅的“老周记”,被高高地挂在了百草胶坊正门的旁边,匾下还立着他当年熬胶用的木勺,底座上刻着“九炼九滤,古法传承”。老周师傅正在教学徒们“扫沫”这道工序,一抬头,看见白景隆陪着济南提督府的师爷走了进来。
“白少东家,好手段啊!”师爷一边环顾着满墙的老匾,一边赞叹道,“一口气就收了二十七家胶坊!”
白景隆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真正的商战,有时候就是这么平平无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正说着,管家捧着账本,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喊道:
“少东家,最后一家‘永盛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