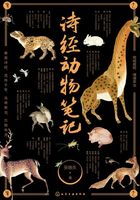
虎:一声虎啸,万念俱灰

一个人可能不了解厨房里常见的蟑螂,却能对老虎侃侃而谈。原因是他自小就听大人讲到老虎的事情。
我记忆中最早出现的老虎,都被武松、孙悟空打死了。与其说它们是弱者,不如说它们顶起了人类的英雄人物。没人把拍死蟑螂拿来炫耀。
老虎对人类早已没有威胁。现在如果你有机会亲眼见到它,也只是一种娱乐,比如在马戏团、动物园。而那种老虎虽然活生生的,却不是“真”老虎。
真老虎在山林岌岌可危,其命运根本比不上偷我们厨房食物的蟑螂。《老子》对此类现象有深刻理解:“弱者,道之用。”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小雅·小旻》)
《小旻》说:不敢空手打老虎。这个道理连武松、孙悟空这么强大的“人”都懂得。可见上古先民多么实诚。现代人的道理花里胡哨,很多都不能实诚表达,得玩点噱头,绕点弯子,否则可能被视为智商不足。
但有一个人玩过火了,乃至后来被全国网民起了个绰号“周老虎”。二十一世纪初,据说他是用一幅画中老虎,在树林里拍照,声称此处老虎回归,生态环境变好了。之后他被判刑了。
不要拿老虎开玩笑。俗话说,虎死威不倒。《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就坐在铺着老虎皮的头把交椅上。下面的小土匪,顶多在屁股下垫一块狗皮、兔皮,否则有犯上之嫌。你看,老虎皮毛都有那么深刻的意义。
这个意义的来源极为深远。青铜器上有关老虎的纹饰很常见,比如饕餮纹。在古代军队的名称运用,“虎”字和“虎”符,也流行千百年。老虎作为一种权威、一种象征,比它作为凶兽更令人追捧和敬仰。

作为生肖的老虎,深得中国人欢心。虎年春节请一批虎娃上台虎虎生风地蹦跳,就是一道好节目。但我更倾向于将这些“老虎”形象认定为大猫,因为人们经常是通过猫去想象虎的。真实的老虎无法表现得如此欢乐,它们严肃的表情、稳重的步伐,已经表明它们对待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
古人正规场合运用的虎形象,大多在正道上:威武不能屈。这与《诗经》里谈虎的气氛,是一致的。轻视老虎,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面对强者,哪怕它是缺乏智商的动物,也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大自然创造老虎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要它做森林之王,而是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有比智商更厉害的东西存在——你暗地里千方百计深谋远虑,一声虎啸就令你万念俱灰……
佛家谈虎,常常是指人性中欲念的可怕。一旦放纵它,就会像虎一样横冲直撞,难以收拾。但真实的老虎也有致命弱点,比如它就怕鸟粪,据说鸟粪会腐蚀其皮毛。
我在清代笔记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乾隆年间江苏宜兴有人研究老虎后,熬制了黏胶撒在老虎常常打滚的草丛里,而老虎爱干净(这一点很像猫咪),不能忍受毛皮粘草,就舔啊舔,最终舔得烦躁、暴躁死掉。然后这个人就能比武松更轻松地获得一只老虎。

在娱乐化老虎的过程中,人们的想象力发挥很大作用。前些年大导演李安拍了个片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我大饱眼福。据说影片中的虎就是象征“欲念”等。但我反复看了之后,觉得还是别这么深刻理解才好,因为整部影片画面的华丽美感,远远盖过了哲思气息。

这一点就像悟空、武松一样,顶多拿老虎来衬托一下人的价值即可。《水浒传》中另一个打虎英雄李逵,其实比武松还厉害,他为老母亲,一下干掉几头。但这件事的名声比不上武松打虎。我个人以为,施耐庵在对李逵打虎的描写上,细节不多,趣味不足,导致李逵打虎显得轻飘飘的——人们在娱乐的时候,事实上根本不在乎什么老虎、李逵、武松,只在乎好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