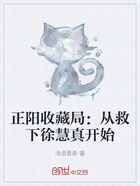
第33章 胡同里的邀约
正阳门的雪还没化尽,小酒馆的煤炉就迎来了两位贵客。石老的竹尺敲着门框,白胡子上沾着未化的雪粒,身后跟着位穿灰布中山装的老人,袖口磨得发亮,却别着枚北大校徽。
“小苏!”石老的声音震得煤炉上的铜壶嗡嗡响,“给你带个贵客,北大历史系的宋伯年教授,看过你修复的《千里江山图》摹本,连呼‘后生可畏’!”
正在擦拭八仙桌的苏浩然抬头,看见宋教授正盯着墙上静理的算术本,镜片后的目光像在鉴定古画:“苏老师的修复术,堪称‘今之张僧繇’,”他忽然转身,中山装口袋露出半截《考古学报》,“北大新成立文物修缮专业,想请你去开两门课。”
小酒馆的空气突然凝固。强子的搪瓷缸停在半空,卖酱菜的王老板忘了擦汗,就连徐老师的钢笔尖都在备课本上洇开墨渍——在正阳门人的认知里,北大是云端的存在,如今云端的人却站在煤炉旁,向中学老师苏浩然伸出橄榄枝。
“宋教授折煞我了,”苏浩然递过牛骨汤,帆布包带扫过桌沿的“步步高升”纹,“我这野路子,怕误人子弟。”他没说,系统界面正闪烁**「检测到学术邀请(稀有度★★★★)」**,但修缮室的《清明上河图》残卷修复进入关键期,他离不开正阳门。
石老的竹尺“啪”地敲在吧台上:“少来这套!”他指向宋教授,“老宋在故宫见过你的修复笔记,说比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还讲究,”他忽然压低声音,“北大能给你配专用实验室,比你那修缮室宽敞三倍。”
宋教授推了推眼镜,目光落在苏浩然袖口的石青粉上:“我们知道你离不开正阳门,”他掏出聘书,“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内容你定——古画修复、器物鉴定,甚至《青囊书》里的中医文物学,都行。”
小酒馆的算盘珠子突然响了——徐慧真正在算酒账,银戒指在“徐记”匾额下泛着微光。她忽然想起,苏浩然给静理补课时,能用《九章算术》讲透修复比例,这样的人当大学老师,怕是要让北大学子疯抢课位。
“苏老师,去呗!”强子的三轮车夫突然开口,“以后我们说起来,也能挺直腰杆:‘咱正阳门出了个北大教授!’”
徐老师的钢笔尖划破纸张,他盯着苏浩然的帆布包,想起自己熬了十年才评上中学讲师,此刻却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宋教授的校徽在煤炉光下闪着冷光,像面镜子,照出胡同里的市井与云端的学术之间,横亘着的那道看似无形却坚实的墙。
苏浩然忽然笑了,指尖摩挲着帆布包上的青铜钥匙:“宋教授,”他望向天井的老槐树,“我的课,得带学生来正阳门写生,”他指向小酒馆,“就像这牛骨汤,得在煤炉旁熬,才有烟火气。”
宋教授的眉毛跳了跳,忽然笑出声:“好个烟火气!”他在聘书上唰唰写下几行字,“同意设立‘正阳门实践基地’,你的课,北大校车每周接送学生。”他忽然凑近,声音里带着学者的狡黠,“不过你得答应,把修复《清明上河图》的过程,写成教材章节。”
石老的竹尺敲着宋教授的肩膀:“老宋你这是抢人啊!”他转向苏浩然,“故宫也等着你的修复日志呢,两边都别耽误。”
苏浩然接过聘书,系统界面轰然亮起:「解锁职业身份:北大客座教授(文明传播+ 30%),激活‘学术经纬’能力」。他忽然明白,这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让修缮室的案头与大学的讲台,在正阳门的胡同里连成一线——就像老槐树的根系,既深扎泥土,又枝叶参天。
“成交,”他握住宋教授的手,注意到对方掌心的茧子,“但第一节课,我要带学生看徐记小酒馆的牛骨汤熬制——那是‘水火既济’的活教材。”
徐慧真的算盘珠子差点蹦起来,蓝布围裙下的心跳得比煤炉还热。她忽然想起,苏浩然给静理讲《论语》时,总把“工欲善其事”与修复工具结合,这样的课,怕是北大学子从未听过的奇课。
暮色漫进小酒馆时,宋教授的校车停在胡同口,车灯照亮“经纬堂”的匾额。石老忽然指着苏浩然的帆布包:“小苏啊,以后去北大,记得带那枚前清举人印章——老宋他们研究科举制度,正缺实物教材。”
苏浩然点头,摸着口袋里的青铜钥匙,听见系统最轻的“叮”声——不是提示,而是无数老物件在修缮室、小酒馆、北大课堂之间,织就的文明经纬。他知道,明天起,正阳门的胡同里,将多出一群穿校服的学生,跟着他在煤炉旁、画案前,读懂文物里的人间烟火。
“苏老师,”徐慧真忽然递来热酒,“明天我让静理画张课程表,贴在小酒馆墙上,”她的银戒指映着聘书的红光,“就写‘北大教授苏浩然亲授修复术’,保准供销社的糖都卖得快些。”
雪又开始下了,宋教授的校车碾过胡同的积雪,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苏浩然望着小酒馆里的街坊,忽然懂了:所谓北大教授,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修画、讲课,而正阳门的煤炉、老槐树、小酒馆,永远是他文明修复的起点。就像手中的聘书,不过是张特殊的宣纸,而他,即将用匠心作墨,在上面画出最独特的经纬。
“石老,”他忽然转身,帆布包在雪光里泛着温润的光,“下次带学生来,让他们给牛爷的青花瓷碗写篇论文吧——破四旧那年的煤堆藏宝,比任何学术论文都生动。”
石老的白胡子抖得像堆雪,竹尺在空中划出个漂亮的弧线:“你这小子,天生该当老师,”他望向宋教授,“老宋,咱们打赌,不出三年,苏浩然的课,能让北大学子把正阳门的砖都研究出纹路来。”
雪越下越大,小酒馆的灯却越发明亮。苏浩然摸着聘书上的北大校徽,忽然笑了——他从未想过成为云端的学者,却注定要做那个在云端与泥土之间架桥的人,让文明的火种,既在讲堂上燃烧,也在胡同里传承。这,或许就是他的“学术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