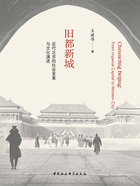
二 市政基础设施
市政建设是民国北京走向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与沿海城市相比,近代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皇室逃离,国都被入侵者控制,但与此同时,北京迈出了建立近代市政体制的实验性一步。联军退出之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借助于使馆区的建设,城市风貌开始发生部分改变。一直到清朝覆灭之前,国都局势相对稳定,铁路、城市道路、电力照明、自来水等在一些区域修建。这些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了市民生产与生活条件,构成了北京近代城市化的物质基础,新式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邮政体系的应用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其上的思想观念与人际关系。
道路改造是城市改造的重要前提。清末之前,北京城内大多数道路都是未加铺设的土路,只有几条大道以石板或条砖铺设,旧京街道以坎坷泥泞闻名,“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19]。清末“新政”时期,北京作为国都,“地居中央则群才所萃,近接政府则教令易施”[20]。为利于行旅,清政府首先拨款在繁华地段和官衙集中的东四、东西长安街、东华门大街、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户部大街等主要街道,采用近代技术修筑了第一批石渣路,逐渐取代原有土路和石板路。其中,东华门大街被认为是北京第一条新式公路,于光绪三十年(1904)由路工局包工修筑。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组织编纂的《北京志》介绍了当时京师之地的道路修筑情况:
近来稍留意修整道路,经工巡局提议,户部特支八十万两,着手翻修甬道,内外城均已大部分竣工。翻修道路的方法,即将原有甬道翻起,使中间及两侧均成同一高度。中间为人行道及轻便车道,左右两侧为重车道,中间左右设沟以便于排水,只有中间路面用条石及水泥,以固地面,左右种植杨柳、设路灯,撤销全部小摊,每隔一、二百米配备巡捕,以维持交通和保障安全……这次重修,可以说是北京道路的一个新纪元。[21]
虽然路工行政机构屡经改组,但修路工作一直未有间断。巡警机构建立之后,各厅建立了清道队,负责维护道路卫生及整修。同时,在主要街道种植树木,并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清末北京道路新式建设规模十分有限,“如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南北新华街、府右街及香厂、万明、仁寿、华严、仁民等路,或地宜商场,限于经济;或路居要津,城墙为障,均未能开辟。而其余繁盛通衢未及展修者,比比皆是”。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将京师各路通盘筹划,“分别缓急,揆度财力,择要次第兴筑”,完成120余段。[22]
在京都市政公所新修公路中,沥青路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21年西长安街改建成沥青路,1928年东长安街改建成沥青路。1936年,在南长街、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由工务局修筑了沥青路面。不过,这些沥青路多为在原有石渣路基础上翻修而成,“新路的扩充,无论石渣路或沥青路,非常之少。北平工务经费,原很支绌,现在只做翻修旧路的工作,已觉人工不敷分配,更那有余力去拓修新公路呢”[23]。所谓新公路基本仍集中在内城中心,外围地区并未有明显扩展,各个区域新式道路分布明显不均,以1930年年底北平工务局的统计为例:
表1-1 北平内外城各区公路统计(1930)[24]

以上表为依据,位居核心区域的内一区与内二区,无论是石渣路,还是沥青路,其长度与面积都远高于其他各区,两区沥青路的长度超过全市沥青路总长度的60%。在这些区域内,先前形容北京道路“天晴时像香炉,下雨之后是墨盒”的景象基本消失,“从菜市口出发,东往骡马市大街,由珠市口而到前门,北进宣武门去西单牌楼等处,早就没有了这种情形”[25]。而外三区竟然没有修筑过一里的新式公路,即使考虑到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形以及公路需要的“先后缓急”,这种对比仍然令人惊讶。
对城市环境影响很大的沟渠整修工程也同时展开,北京沟渠,一般所谓筑成于明代。清代,管理之权,属于工部之值年河道沟渠处,掏挖之责,归于步军统领衙门。民国建立之后,疏浚沟渠之责转自京师警察厅。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设工务科兼管沟渠水道之改设事项,“先从测定水平入手,当将大小各沟渠一律勘测,并按照水平方向,择其繁要各处,或修浚旋沟涵洞,或添筑暗沟,沟路务期脉络贯通,高下有序”[26]。大明濠全长5300公尺,“年久失修,沟墙多已坍塌,行人车马时虑倾踬,且邻近居民任意倾倒秽水,致臭气日溢,于交通、卫生两有妨碍。前市政公所于民国十年起逐段改筑暗沟,陆续修至石老娘胡同西口,上铺石渣,以利交通”[27]。北平市工务局成立之后,继续修筑前述未竣工之处。大明濠改为暗沟之后形成街道,东交民巷玉河、北新华街等沟渠也先后改造为暗沟。
国都南迁之后,地方政府对市政的投入减少,北平的城市道路建设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而言,民国北京道路建设主要集中在内城繁华地区,沥青路与石渣路长度有限,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路仍然占据更大比例,“人从屋内轮脏物于道路,风由道路又将脏物轮回。尘土因着这种轮回,便继续的存在。到下雨时,尘土虽然没有了,然而因为没有新式沟渠的缘故,道路遂不免成了泽国,水退后,街道上又是泥深数寸”[28]。抗战结束后1946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北平全市已修道路687公里(东西郊新市区不在内),其中沥青路占32%,石渣路占22%,土路占42%。[29]
道路建设不仅塑造了都市景观,而且也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建设,对外国侨民和本地上层人物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东长安街一带迅速发展,民国初年已经成为最能体现北京都市繁华的代表性区域,出版于1919年的《实用北京指南》介绍:
外国使署及其商业,多在东交民巷及崇文门内一带,楼阁雄壮,街衢整洁。内城繁盛之区,以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地安门大街为最,商店林立,百货云集,往来游人盘旋如蚁。故都中有东四西单后门(即地安门)一半边(买卖大街常在大街东半)之谚。他如西直门内之新街口,东直门内之北新桥,东安门外之王府井大街,亦为商肆集聚之,惟较东四西单等处为逊耳。平日游览之所,则有东安西安各市场,而东安尤盛。茶楼、酒馆、饭店、戏园、电影、球房以及各种技场、商店无不具备,比年蒸蒸日上,几为全城之京华所翠矣。至若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等处,每届庙期,游人麇集,亦几如市场也。夏日消暑,则有什刹海、积水潭,堤柳塘莲,风景清绝……[30]
同一年成书的《京师街巷记》对此描述:
东长安街,别于西长安街而言,指由东长安牌楼起至东单牌楼下东西一段大街之谓也。前清光绪初年,有如此宽阔。自庚子年,拳匪肇衅,联军入城,两宫西狩,遂结北京条约。我国失败。使馆界于是大为扩充,将头条胡同亦辟为公地,谓之公地。今只有二条三条,无头条之号称也。公地一带,树木葱郁,绵互东西。夏日之间,浓荫蔽多有于此乘凉者。马路迤南,为使馆界,有铁丝拦阻。警厅竖立界牌,名曰保卫界内,禁止穿行。外凿浅沟,内中青草荒芜,时有日军操演。公地以北,楼房栉比。东端有东菜市,系市政公所设立者,早间商人拥集,买卖殷繁繁。迤西有四号妓馆,系外人营业者。公司之中,以美丰汽车公司为最。英商普利皮带工厂次之。外又有福德汽车行,在妓馆之东。此处饭店最多,若东安饭店,及大餐厅,长安饭店,电报饭店,北京饭店,皆系饭店中之著名者,然多系外资。永亭铁厂,在美丰汽车公司之旁,亦系铁工厂中之可数者。旧东安饭店西,有平安电影公司,为京都电影中之第一者。政务机关则有一等邮务局,京汉铁路局,电报总局。[31]
瞿宣颖的外地友人在游览北平时感叹东交民巷的“纤尘不染”,当时的都市地理丛书之一的《北平》描述1930年代的北平街道:
北平的街道,都非常广阔,著名的如东长安街、西长安街、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东单大街、西单大街,以及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等,都是柏油大道,其宽度比上海的各马路至少要阔上一倍,街道两旁,植着森绿的行道树,人在街上走,仿佛在一个大公园里散步。这些街上,多半都有电车通行,如果要出门去,雇洋车也很方便。不过每逢初春或深秋时节,北平城内的灰土很大,迎面乱吹,好像重雾。尤其是胡同里的街道,满积着泥巴,天晴变成灰土,天雨变成泥浆,使人不论在晴天或雨天,都有“行不得也”的感想,这可说是北平生活上的一大缺陷。[32]
与道路建设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意义不同,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等更能在细微处改善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
1871年,丹麦、英国商人开始在上海经营电报业务,光绪八年(1882),津沪电报线路延伸接入北京。至清末,作为国都的北京已经成为全国电报总汇中心,布政令于四方,不仅可以通达国内各省,还可与法、俄、英等国实现连线。民国建立之后,北京政府建双桥无线电台,1925年正式投入使用。
庚子年间,为满足军事需要,德国军队架设了北京通往天津塘沽的电话线,同一时期,丹麦商人也开始在北京经营“电铃公司”,从事京津地区的电话业务。1903年,清政府架设了一条通往颐和园和各兵营的电话线,这是北京最早的自办专用电话。1904年,北京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电话局开业。1905 年,北京电话总局成立,城内城外有两处分局。此后,北京的电话事业陆续扩展至南苑、香山、汤山等地,并开通了上海、武汉、南京、奉天等地的长途电话。至1918年,“京师用电话之户,止于七千五百,不足万家,吾国电信事业,尚未发达也”[33]。
北京的电力照明首先从宫廷开始使用。1888 年,慈禧太后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在整修西苑三海过程中,增加了一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电灯便是其中之一。1889年,慈禧所居的西苑仪鸾殿(今中南海怀仁堂)亮起了电灯,即为北京城市电力照明之始,“西苑电灯公所”也正式建立。1890年,“颐和园电灯公所”也建成,全套发电设备由德国进口,开创了北京最早的小型发电厂。19世纪末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使用电灯照明。庚子事变之后,英国洋行在东交民巷台基厂三条建造瑞记发电厂,向使馆区供电。此后,北京电力工业由宫廷照明用电发展起来,许多高官府邸安装了电灯,如醇亲王府、瑞麟的府邸也开始使用电灯。
1904年,由几位华商发起,经农工商部奏准,成立“筹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这是北京首家服务于一般市民的发电企业,两年后建成发电。此后,北京内外城一些主要街道和部分商户开始安装电灯,供电服务范围扩展,逐渐从宫廷、使馆、军政机关、商户转向民用。1919年又于京西石景山兴建发电厂。此后,公司在通州再建发电厂,并在铁家坟与西便门设开闭所,改善了因线路较长、供电距离较远而造成的电压过低、不稳、亮度不够现象。
北平市政府建立之后,电力事业开始有较大发展。当时,煤油价格上升,在经济因素驱动下,商户、居民相继改用电灯,据统计,1929年,全市使用电灯用户数为21116户,占全市总户数的7.8%。1930年开始实行电灯包月,每月按盏数计费,每盏1元。同时,公司还推出优惠政策,实行电价递减制,每月消费超50元者,给予折扣。[34]电力照明使用初期,供电范围主要集中在内城核心区域,而在外城以及城市边缘地区,电力的使用还非常有限,直至抗战前夕,北城以及青龙桥地区才出现变电站。
同时,电力还应用到北平城市道路照明领域。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多不设路灯,只是一些商户在夜幕降临后于自家门口挂起灯笼,照亮一隅。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京街道开始出现路灯,主要为沿街商铺在自家门前点燃煤油灯。“京师华商电灯公司”营业后,首先在东西长安街、西四、东四、前门、崇文门等繁华商业地带安装电力路灯,一些街巷胡同的煤油路灯也逐渐改装为电灯。电力照明的广泛使用,使城市夜晚呈现出不同于白日的另一种景象,斑斓的灯光不仅渲染了都市的繁华,更极大增添了诸多生活内容,“夜生活”的概念随之产生,人们的时间观念得以扩展,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
饮用水作为维系生命的基本保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明清时代的北京,“上等之户及禁廷饮料,多取之玉泉山、西山各名泉。耗资既巨,输运极艰”[35]。由于缺乏大的河流体系,京城的居民饮水主要靠土井,井入地下不足3米,水质偏碱,多苦而咸,称“苦水”。整个京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口深井可以提供无苦味的井水,称“甜水”。“平市井之以甜水著名者,初只有安定门外之上龙井,南城之姚郭井,次则东北城之中心台,东厂胡同之西口,灯市口之老爷庙,各有一甜水井。自清光绪庚子年间,有一日本人在东四十二条西口用新法凿井,较天然之甜水井尤佳,且随处皆可开凿。于是洋井之风大开,日人包凿洋井,颇获厚利。而凿井新法亦遂流传于市内。凿穴安管以及考验地底之砂层泥层诸方无不深悉。并鉴于日人所用竹管年久易坏,一律改用铁管。市内以新法凿井为业者渐盛。井商所开之井亦日多,因此以井水为业者乃增至一百余家。”[36]
1908年,农工商部奏请筹办自来水厂,“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迭经商民在臣部禀请承办”[37]。周学熙创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温榆河为水源,在东直门外及孙河建水厂两座。公司以招商集资的办法,集得资金300万元,同年 5月开始筹建,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并在城内各街巷埋装水管,两年后正式供水。1910年,军机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参观东直门外自来水厂描述:“厂地宏敞,水塔高十八丈,壮丽可观。”[38]
自来水供水系统的出现,改变了北京城传统的供水方式,“机关一启,汩汩其来,飞珠走雪,如天然之泉脉,巨室既引之,厨房、浴室亦联于铜管,取之不竭,足食足用。各大街之口,亦有龙头,由附近铺户代售”[39]。不过,由于公司采取商业运营方式,缺乏来自官方的有力支持,水价较高。加之北京市民多数长期饮用井水,对自来水这一新生事物在认识上存在疑虑。此外,又遭遇以贩运售水为生的山东水夫群体的联合抵制,致使自来水的普及率一直受到限制。
1931年,孙河水厂停用蒸汽机,改用电力送水。由于用水安全与居民生活关系重大,北平市相关管理部门社会局以及卫生局对此加强监管,初步建立了质量保障体系,改善自来水水质,并采取一些其他配套措施推行自来水,“本市人口日繁,而自来水供给区域及数量,迄未增加,推厥原因,不外自来水厂本身业务,未能努力随时进展,而城内私有水井任意添建,实为莫大障碍。除饬处会同社会局督促水厂改良,以期发展外,一面严格限制添建水井”[40]。市政当局对于卫生也更加重视,“自来水—项,时常化验,务使水质清洁,免害市民健康。于是北平饮科,咸称利便”[41]。除此之外,自来水开始应用到城市消防、街道清洗、树木维护等公共领域。
近代公共交通兴起之前,北京城处于“步行”时代,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有限。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大多数普通居民出行没有代步工具,只有少数达官显贵乘坐轿子或骡马车,与这些交通工具相对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市内道路、桥梁等也处于低级水平。清末时期,空间扩展、人口增加、经济总量增大,商品经济发展增速,城市规模明显扩大,原有的交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从人力车到电车和公共汽车,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开始出现在北京,从而引发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北京城市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式交通工具开始引进之后,北京开始建立公共交通体系。1921年,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办,1924年底,第一条有轨电车从前门经西单至西直门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全长9公里,共有10辆电车运行。1925年,北京有轨电车新增5条线路。电车开通之时,作家丁西林描述,由于票价较高,乘客很少,其中大部分只是偶尔为之的政府官员、贵族学生和游客。[42]1929年,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合伙捣毁电车的社会事件。不过,有轨电车事业虽经打击,还是逐渐被市民接受。[43]
19世纪末,京奉铁路段中由天津通达京师西南卢沟桥的津卢铁路以及卢沟桥至保定的卢保线先后建成。之所以远离京师核心之地,主要为避免火车对紫禁城的“侵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之后,英军为了运送军队和物资,率先将津卢线展修至皇城正南的正阳门东瓮洞内。不久,卢保线也被延长至正阳门西瓮洞内。1905年,北京至汉口铁路通车,1909年,北京至张家口铁路通车。随着京奉线、京汉线、京张线、津浦线等铁路的先后建成,北京逐渐成为连接东西南北交通的全国铁路交通枢纽。
铁路兴起之后,极大促进了人口与资源的大范围流动,对于铁路沿线城市产生重要影响。京津铁路贯通后,给两地居民带来极大便利,两地交流日益频繁,《申报》称:“天津去京仅二百四十里,向以车烦马殆,故往来游玩者殊属寥寥。现在铁路通行,京城内外附近居民,咸思到津一扩眼界,其中以旗人妇女为最多。津地大小客栈,几于满坑满谷。”[44]北京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城市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1919年后北京还陆续开辟了至高丽营、通县、三河、玉田、丰润等地区的远途汽车。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为了便利城市交通,弥补城区电车运力不足,以及发展旅游事业,开辟城郊旅游区的需要,组建了北平公共汽车筹备委员会,后改称北平公共汽车管理处,订购大客车30辆,先后开辟了5条运营路线,标志着北京城市公共汽车的开端。不过,由于北京城市传统结构特点,公共汽车并不能有效通行,利用效率不高。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始筹划修筑环城铁路,1916年1月1日正式通车。环城铁路所环之城为北京内城,起点为西直门,“利用者,惟东北之朝阳、东直、安定、德胜四门。此四门城内皆街巷稠密,城外亦有大街、商场、马路,若外城除永定门有京奉铁路、京苑铁路,广安门有京绥铁路外,左安、右安及广渠门大抵城内亦多菜园、荒地、坟墓。城外民居尤少,客货必比内城更少,是以勘测路线,不绕外城”[45]。环城铁路与京张铁路、京奉铁路接轨,西直门站为京张铁路起始站。环城铁路修建之后,对于北京城内的人员出行及货物运输都带来了便利。
现代汽车在清末就已传入北京,宫廷是最早的汽车用户。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4月30日,世界早期汽车赛中重要赛事——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在北京举行。参赛汽车从德胜门出发,有当时新兴的四轮汽车,也有早期的三轮汽车,全程横跨欧亚大陆。1908年春,商人吴廷献呈请在京师开办市内汽车载客业务,但京师巡警总厅以道路设施未达配套拒绝了这一申请:“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唯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若遽准行驶,不特危险堪虞,且于车马殊多窒碍。”[46]1913年,北京出现了第一家小型出租汽车行,至1933年,北京有汽车2710辆。[47]
表1-2 1930年代初期北京交通工具基本数据

续表

新式公共交通的兴起对北京城市生活的影响非常广泛,首先,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其次,使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市民的时间观念发生变化,开始从模糊变得精确,钟表的需求逐渐上升。尤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时间与效率的要求开始严格。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生活半径明显扩展,日常生活的内容大大增加,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可以说,以人力车、电车和公共汽车为代表的公共交通的兴起与发展,是民国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路面狭窄,设施较差,人行道与车行道不加区分,有轨电车、汽车、骡马车、人力车、行人混杂其间,对于建立规范交通秩序的需求日益迫切。
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对这一时期北平的市政建设给予了如下评价:
北平昔有首善之称,政府所在,人烟稠密。故市政建设,自较他地优良。平市警察,向推为全国第一,有模范警察之誉,但近来亦无显著之进步,不过墨守成规而已。政府南移之后,北平有改为教育区之议,但未实现。后市政当局,拟将北平改为游览区。对于本市古迹,及名胜,均竭力提倡保护,并加修葺,如正阳门、五牌楼、前门内东西交民巷、东西长安街及东四、西四、东单等牌楼,各坛庙,均一律重修,漆油彩画,以重观瞻,而吸引游人,藉为繁荣市况之一助。现平市对于路政,尤努力改善,前外大街,及西单大街,加宽马路,拆除宣武门瓮圈,便于行人。至于交通伞,标准钟之设置,市容气象一新,较前进步多多。至于卫生事项,亦积极注重,设计周详,正迈进中,其他如慈善团体,官方亦多协助,官营公共汽车,前由平市府计划实现,秦绍文任市长后,为救济人力车夫生计,曾将城内一二两路汽车停驶,其香山西山两路游览车,照旧开行,并增添南苑小汤山两路,其春节临时开驶者,有白云观,财神庙,大钟寺等处,南苑小火车,亦于元旦日恢复,每日往返三次,不特便于游人,而本市交通进步较前颇有可观耳。[48]
清末民初是北京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基于经费投入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市政设施集中在内城和外城前门一带的富庶、繁华地段,对于其他区域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则无力顾及,现代市政建设体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普及程度一直有限,成果无法惠及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以电力照明为例,宫廷是最早的用户,后来逐渐扩展至私宅,供电范围主要集中在内城核心区域,外城以及城市边缘地区的使用非常有限。1920年代,电力路灯已经开始用于北京城市道路照明,但范围也仅限于东西长安街、西四、东四、前门、崇文门等繁华商业地带,内城其他一些街巷仍多为煤油路灯,而外城大部分地区夜幕降临之时仍漆黑一片,导致内外城生活节奏的不同步性。
自来水供水系统的出现,改变了北京城传统的供水方式。不过,受制于价格以及其他因素,北京自来水的普及程度一直十分有限,“中上之户,多皆装设自来水,饮用悉属安全,无复知旧习之为害”[49]。1922年,北京安装自来水的用户只有5000余户,只占全部户数的3%。1934年,全市已铺设水管380公里,饮用自来水者9600余户,但与当时北平的20万户居民相比,不及5%。[50]“并非城市中的每个人都从道路工程中平等受益;相反,道路改造工程导致了一种新的按等级划分的空间组织形式……一个新的、在空间秩序中得以表达和确认的社会等级制度清晰地出现在这一系列转变当中:养路费用分配不平等,富人区更多受益;沥青马路极少甚至很可能根本没有修到过贫民区;速度的快慢取代了交通工具的奢华程度而成为了决定社会等级的关键。尽管交通和街道工程都是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名义进行的,它们带来的却是新形式的社会分层。”[51]当时北大社会学教授陶孟和感叹:“北平号称现代繁荣之城市,已有电灯、电报、电话、电车、自来水及无线放送之设备,其贫民家庭乃生活于如此简陋之物质环境内,仅以本地制造业之出品,已足供给其需要,则内地大多数之农民,更何能希望得到较优美之生活。”[52]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为北京市政建设的发轫时期,在“新政”的推动之下,京师之地的市政建设初步开启。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北京的市政建设有所提速,但由于外部局势动荡以及财力匮乏,北京自身产业基础薄弱,经济驱动力不足,市政建设成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