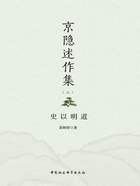
七 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
我现在书案上放有三件东西:①98岁高龄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的新闻报道,去世时间为2016年7月8日;②他的《世界史》中译本(施诚、赵婧译),由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58.5万字;③我的《老学日记》第九编第228节《麦克尼尔的文明观念》,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三件东西放在一起,特别是这位已经是“坐九望百”的老学人的去世,引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追思。他是位“文明互动”论的倡导者。早在2012年10月13日,我研究他的文明观念时,关注他的两本著作:《瘟疫与人》和他与儿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瘟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写入了历史。尤其是父子二人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把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问题,放在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进行研究,这和我的“文明交往自觉”思考不谋而合。这使我产生了同道者之间那种亲切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开篇即叹道:“知音其难哉!”我正是怀着知音的心情写这篇追思短文。
早在2012年1月,我在3卷本《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六条交往网络”: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我在《文明交往自觉论纲》中谈道:人类文明发展有两种动力,即生产力和交往力,而且生产的前提是交往,交往力是广义的生产力。我认为:“这六条交往力网络所形成的交往的合力,比机械网络更复杂、更多变、更生动和更有力。因此形成的文明交往史更具有壮丽风采和恢宏气象。”[4]
在2012年10月13日这篇《老学日历》中的《麦克尼尔的文明观念》短文中,我记下了两个联想:关于人类文明交往研究的三个层面(思想情感、文化理性、文明自觉);人类文明交往的平衡点与契合点问题。当时,我并未读到他的代表著作《世界史》。现在我看到的是第四版的中译本。这是一本有影响力的教材,其特点是把人类历史作为一部文明发展的整体历史。它视野广阔、文笔简洁,尤其是以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为线索,此一理论创新引人注目,令我感到特别亲切。
威廉·H.麦克尼尔生于加拿大温哥华,20岁迁居美国芝加哥,21岁和22岁分别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30岁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他和世界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都在研究世界史和写世界史教材,而后者任教的芝加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是与他互相交流、争论的不同历史学派。我记得已故的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曾同我多次谈过此事,他认为除了他自己为总主编的《世界史》教材之外,中国也应有不同观点的,并应有个人写成的《世界史》教材。他也曾建议我以人类文明交往为线索、以简洁生动文笔写成另一部中国风格的《世界史》。他甚至还自荐为此书写一篇长序,以显示中国世界史领域内的百花齐放特色。遗憾的是,我一来能力、水平不够;二来当时正在主编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和1卷本《中东史》,无暇他顾,所以有负厚望,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友情之债,至今思之,心存遗憾,无法面对他的在天之灵。
的确,世界历史教学之本是世界史教材。世界史教材的质量是研究成果的积累与综合,是有自己学术特色和风格,并且寓论于史,同时文字流畅易懂。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有其积累的基础,这就是他之前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尤其是《西方的兴起》这部被称为“人类共体史”的著作。历史分期是他书写《世界史》的线索路径,具体提纲是:①远古时代至公元前500年为“旧大陆四大文明”(中东、印度、中国、希腊的犹太教、佛教、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②中世纪的文明平衡时代(四大文明向周边地区扩张,程度上势均力敌又各自独立发展;夹杂有希腊化、伊斯兰扩张、蒙古扩张);③1500—1789年西方文明支配时期(西方的海外扩张);④1789年至今,全球走向一体。这是一个有自己见解的独特体系。
约翰·R.麦克尼尔称,他父亲把1967年初版的《世界史》作为《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其特点是“短小”,而《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003年版)的“篇幅要大得多”。据他的观察,写世界史是他父亲一生的志向。这正如《世界史》第四版序言(1978年6月)开篇所讲,《世界史》教材的生命力在于:①从“人类文明”这个简单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历史以整体的叙述,容易理解;②“清晰简洁的文风”。这是值得称道的风格。
在时间观念上,写世界史是从远古一直到当今发生的大事件。据此原则,新版增加了第30章,其目的是关注“基础的、根本性的变化”,以少纠缠细节而努力延长“保质期”。写通史要通到当今,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这部研究生教材中,就是写到付印前中东发生的重大事件。我是用“写实的方法”,处理当代史这一敏感问题。
人类社会有过而且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因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但人类“文明”所指的是“大型社会”。这是对的。因为文明总是社会文明,尤其主要的是制度性的社会文明。此种“大型社会”文明包括:①把千百万人组合在一种松散但清晰的生活方式之中;②地域覆盖数百乃至数千公里;③时间跨度,相比个人的寿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他认为,人类社会第一次达到“文明的复杂程度及其规模的时代开始算起”,旧大陆主要文明传统只有四个,新大陆出现的不同文明不超过三个。这个重点也对。
何谓“西方文明史”?美国教材已经达致共同认识;而何谓“世界史”,却无一致标准。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他的世界史是“整体世界史观”的简明世界史,其“优点是一以贯之、清晰明了,能够被掌握、被记住,过后可以回味”,这四个优点,尤其是第四个“过后可以回味”很有意义。这里,他的历史观的文明结构理念是:①“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平衡都容易被打破,推动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创造了非凡的或强大有力的文明。”②或多文化中心的“邻居,抑或邻居的邻居,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技术或观念,但更多的情况,是加以调整和改变,以便为顺利适应当地的环境”。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主要文明中心,“首先研究最初的一个或几个抵抗中心,然后考察对文化创造的主要中心所产生的革新,世界上其他民族在(经过直接、往往是间接渠道)认识或体验之后,做出反应或反抗,进而我们就有可能对世界历史的各阶段进行概括。”④“从这一视角看,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路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有关古代的交往关系,现存的文献记载有时会模糊不清,但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和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威廉·H.麦克尼尔的历史观念中的古今观,集中在对“个人判断力”的一种锻炼培养上。他认为,古代史的判断力有“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可以指引我们通往久远历史的路径。与此相反,我们自己却因为年代太近,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历史学家在处理近期事件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他客观冷静地对待1998年4月新写的第30章《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因此,新写的第30章是否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与许多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分享——尽管不是那么舒心如意——的世界,就有待其他人的判断了。”
对此书的“指导原则”,他的儿子约翰·R.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他回忆说,当他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世界史的时候,就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5]可见,“联系”是麦克尼尔父子历史观念的关键词和哲学概念,而具体到文明观上,应该就是我理解的“人类文明观”中的内外互动“交往”。我的文明观与其他文明观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观念”,而不是一般的“人类文明观念”。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了我主编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特别是我主编的一卷本《中东史》,多年来已是研究生的推荐教材。这一点与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历史观念相近而又不同。我们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科研群体,从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自觉的历史观念的理论视角,在史论结合上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我在追求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道路上,威廉·H.麦克尼尔的历史著作和思想,给我的启发是很可贵的。理解一位学者,读懂他的著作,需要机缘,也需要心灵相通。观察问题,需要有广阔的世界眼光,是学习世界史不可少的。研究问题,需要有深远的人类文明交往自觉视角,学习人类史也是必需的。如何研究世界史、人类史,如何在高处站、往深处思,又如何以厚实的历史感为基础、又合乎时代精神,从而得出称得起有新意的原创性思维成果,我从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的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互动的路径中,遇到了知音。这有点像他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相遇一样,我在中国西安西北大学也唱出人类文明交往互动之歌:“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
在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逝世悼文的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他是一位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在改变人们思想和大众公共行动提供依据方面,历史学家能发挥作用。‘历史学’是一个很高贵的名称。根据我们的阅读和反思,告诉其他人,世界上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种荣誉。”他是一位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在人类文明互动问题上有实质性建树,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在世界史学术领域中建立一座丰碑。我们不能要求他成为一位有系统文明交往理论的思想家,然而如果他再向此方向努力一步,将会有更卓越的成就。他又是一位谦虚而严谨的学者,他自信而又自知,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著作看成定论,他一生都在深化、细化自己的学术思路,不断完善自己的著作。在人类史、自然史世界中寻觅,我想这都是在世界史、在人类文明史的学术坐标上给予他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