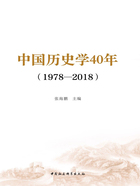
新中国考古发现及其对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贡献
陈星灿
90多年前,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1891—1962)在《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就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1]90多年后的今天,不仅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渐渐由考古学发现而得以不断重建,就是东周以后的古史,如果脱离考古学的发现,也将失去它应有的光彩。关于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千年前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年)所著《史记》,写中国历史的开端《五帝本纪》,共用了4660字,接下来写《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分别用4171字、3661字、10400字[2],可1999年主要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用了1148页,而这还主要是有关商至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约公元前1570—前221年)[3]。这样比也许不够恰当,因为古今历史的叙述方法完全不同,但是,说目前的中国上古史(秦汉以前的古史)差不多完全是由考古发现支撑起来的大厦,恐怕并不为过,因为今天历史学家掌握的传世文献并不比司马迁多,除了考古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外,历史学家赖以研究的甲骨、金文和简帛资料,也多是近百年来考古发掘的产物;后者跟一般考古资料一样,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
另外,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开始,中国史学家就开始自觉地把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相结合,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王国维把这种结合比喻为“二重证据法”[4]。与20世纪初期以前的历史著作不同,目前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述,都离不开考古资料的支持。甚至有的历史著作本身就完全是由专业的考古学家完成的[5]。当然,考古学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特别是事关商周及其以后时代的,也多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帮助;脱离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有的考古解释好比郢书燕说,完全误入歧途。难怪有学者这样说,“无视考古发现的史学家会很快发现自己落伍了,而对传统文献不熟悉的考古学家,也将失去很多赋予他或她的发掘品以灵魂的机会”。[6]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目前也存在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的做法,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是大家公认的。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甚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无法脱离考古学而单独存在[7]。时代越靠前,对考古学的依赖就越大。在这篇短文里,我无法将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及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贡献一一报告给大家,实际上我也没有能力做这样一个全面的工作;我只能就我熟悉的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某些重要发现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等方面的传统认识,略加叙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一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
除了极少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尽管在中国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众多的远古人类的化石材料,年代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但是很少人会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源头推到这个时代。不过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大量材料表明,中国的古代居民从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直至近代种族的同质性比较明显。这种特征尤其表现在黄河流域,因此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曾被称为“原始中国人”,或“第一批中国人”;而中国南北方人类种族形态的差别,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学资料中[8]。如果说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初见端倪,那么原始的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中国这块历史舞台上。
1949年以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只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北方地区的所谓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东部发现龙山文化以后,提出龙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二元对立说”,即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殷商文化应该到环渤海湾一带来探求,这个地区“或者就是中国文化的摇床”[9]。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了仰韶文化经由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成为龙山文化的证据,因此,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就在晋陕豫交界地区,也就是传统上被称为“中原”的地方。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10]这个观点,与史学上的中原中心论密切配合,确信所有高级的文化发明,都是从中原地区传播出去的。这种观点支配着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的考古发现和开放的学术环境打破这个一元说,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或“区域文化多元说”的理论模式。[11]
1981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个区,即陕晋豫临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说提出公开挑战。他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2]
以区系类型理论为代表的“多元说”,强调各地区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在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又注意到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中原文化的核心作用。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对此做过很好的总结。他也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大同小异的六个区域:“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就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做第三个层次。……好像是第二层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该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又说,“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一个分层次的向心结构,而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因此,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13]
总之,过去近7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差不多完全是由考古学得到的、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概念,却是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的重大挑战,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参考价值。
二 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问题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考古学也证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14]。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复杂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以中原地区为例,复杂社会的开始,早在第四千纪的中晚期,也就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先是庙底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强力辐射,接下来则是公元前三千纪前半黄河上游、下游、长江中下游、以长城为重心的北方地带等周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扩张和影响。在这种同周边文化的不断交流和互动中,也可以说是在周边文化的压力下,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加强,渐得优势,最终脱颖而出,形成灿烂的二里头文化[15]。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文明,都有深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从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开始,中国的许多区域都发展出大大小小、相互竞争、彼此交流的王国来。夏商周只是在黄河流域众多史前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相对立的政治集团。按照张光直(1931—2001)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16]。尽管如此,目前考古学上所认定的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的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还没有发展出与二里头遗址同等发展水平的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被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17]。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郑州以西的河南中西部地区和晋南地区,范围有限。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河南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政治疆域空前扩大,商文化影响区北及辽河,南达两广,西南到甘青地区和成都平原,东则包括胶东半岛。周代由于分封制的推行,政治疆域进一步向四方扩大,最终奠定了秦汉统一的物质基础[18]。
历史上被长期忽视的长江流域,也有众多实力强大的方国存在。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文明、江西新淦发现的大洋洲文明,都应该是当地土著文明的突出代表,且同中原夏商周文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19]。这些大大小小的方国,经过两千多年的激烈竞争,到公元前一千纪末期最终汇入秦汉帝国的历史洪流之中。
如果说中国史前六大文化区的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文明的主要部分,如果说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形成有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文化共同体,那么,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考古所见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新中国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21]。
三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环境和机制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土著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加以描述。这些特点,跟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决定了这里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处于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虽然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还不能称为中国文化,但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原始文化,似乎走着与旧大陆西侧完全不同的道路。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与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但整个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器时代,中国文化仍旧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作为腹心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及其临近地区,通向旧大陆西侧的道路,被青藏高原和众多的高山大漠所阻隔;向南的道路,又有一系列的高山大川和热带雨林为屏障;东部在史前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茫茫大海;而北方不仅有一望无际的高寒和沙漠地带,还有一系列东西向的大河通向大海。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又是由一系列高原、平原、盆地、山脉、丘陵、河流、沙漠、沼泽、湖泊等构成的数量众多的次一级的小地理单元组成的。地形上的东西三级阶梯和纬度上南北相差30多度的空间距离,构成了从热带到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以及青藏高寒带的差别明显的气候带,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形成特色显著的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又以各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22]。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实际上,即使有高山大漠和茫茫大海的阻隔,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比如,马和马车都是在商代晚期才突然出现的;小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突然出现,到二里岗早商文化(约公元前1600—前1415年)时期,差不多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寻常作物;红铜和青铜器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甘青、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中国没有经过旧大陆西部漫长的红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山羊和绵羊也是从龙山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开始出现,在二里头(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和二里岗时代流行起来,成为常见的家养动物;殷商晚期都城安阳所见的玉器和龟甲,则被认为和目前中国疆域的西部和南部边疆——新疆和南海有关,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则可以追溯到印度洋中。最近的研究显示,家养水牛也可能是公元前第一千纪从印度次大陆引进而来的[23]。
至于秦汉及其以后时代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考古上的发现更多,但是无论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直到18—19世纪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之前,都远远比不上这个巨大地理单元内部各文化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冲突。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甚至更早,栽培水稻已经进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粟、小麦和豆类等旱地作物为主辅以少数水稻栽培的华北农业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600—前1300年前的商代[24];以二里头青铜器为代表的体现祖先祭祀的礼器文化,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的商代,迅速扩张至广大的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超越各地方土著文化,构成一个范围广大的“同质文化”,形成界说中国文明的上层文化基础[25]。
总之,中国文化的基础形成于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它的土著性、多元性和一体性跟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这个巨大地理单元本身跟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文化单元,尽管整个古代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几乎没有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新中国近70年来的众多考古发现,成就巨大,有目共睹。如果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古代文献(特别是《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那么此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则使不少学者减少了对古代文献应该抱持的审慎、批判态度;20世纪初叶的疑古思潮,差不多完全被乐观的信古所取代,最极端者,就是把某些考古遗址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某些传说人物对号入座。考古当然可以证明古代文献的真伪,但这只是考古学能被利用的一小部分价值,它更应该是用它自己的方法和证据,重建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也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差不多60年里,中国的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花费了很大气力去证明二里头遗址是夏的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完全达到,因为没有任何出土文字资料可以确认这种说法。但是,从考古学上看,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了解黄河中游地区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的历史进程;无论这个文化是否代表夏,无论这个遗址是否代表夏的某一个都城,我们都可以肯定在这个时代,有一个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拥有众多夯土台基和围墙,出土高等级的墓葬和青铜器、玉器的国家社会,出现在了伊洛平原的沃土上;考古学的发现还证明,这个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地区,但触角已经伸向长江流域,它的目的可能是控制铜和绿松石这样重要的自然资源[26]。而这些,是考古学出现之前的古史研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晓的。
我想说的是,考古学有它自己的方法和目标,它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对中国历史的重建做出它的贡献。
[1].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2年版(1926年初版),第22页。
[2].不同版本略有出入,本统计采用了漂泊的树电子书二十四史版本《史记》(2006年),其中包括标点符号。
[3].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
[4].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重印本。
[5].比如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就是由三位专业考古学家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写成的。
[6].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Introduction,In 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p.13.
[7].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鲁惟一和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都采用了大量考古材料。更不要说大家熟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了。由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多达11卷,考古资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8].韩康信:《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1—779页。
[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1935年,第1093—1134页;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册,1931年,第556—557页;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0—227页。
[10].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见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114页。
[11].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第6—9页;Chang,Kwang-chi,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n 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pp.37-73;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第10—17页;Liu,Li and Xingcan Chen,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3;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2].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3].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见氏著《史前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14].Liu,Li and Xingcan 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Duckworth,London,200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1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页。
[17].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18].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Liu,Li and Xingcan Chen,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12;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20].陈星灿:《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页。
[21].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Keightley,David N.,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Reflections on How it Became Chinese.In Paul S.Ropp,ed.,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5-5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2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见氏著《史前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陈星灿:《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87页。
[23].Lee,Gyoung-Ah,Gary W.Crawford,Li Liu,and Xingcan Chen,“Plants and people from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pp.104,1087-1092.陈星灿:《作为食物的小麦——近年来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及其重要意义》,《中国饮食文化》2008年第2期;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459页;陈星灿:《公元前三千纪至两千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考古学的证据》,《文物》(韩国)(2018),第231—252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梅建军:《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54页;Crawford,G.W.,East Asian Plant Domestication.In Archaeology of Asia,edited by M.T.Stark.Blackwell Publishing House,Malden,2006,pp.77-95.Yuan,Jing,The Origins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in China,Paper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Zooarchaeology,Zhengzhou,July 13-15,2007.袁靖、罗运兵:《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9页;[美]大卫·安东尼:《马、车轮与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张礼艳、胡保华、洪猛、艾露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刘莉、杨东亚、陈星灿:《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24].Lee,Gyoung-Ah,Gary W.Crawford,Li Liu,and Xingcan Chen,Plants and people from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7,pp.104,1087-1092.
[25].Allan,Sarah,“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6,No.2(May),2007,pp.461-496.
[26].Liu,Li and Xingcan 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Duckworth,London,20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Liu,Li and Xingcan Chen,The Archaeology of China:From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12;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