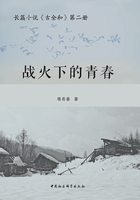
第14章
太阳从正南而西南,从西南而正西,眼下它正在徐徐下沉。硕大的红太阳,只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而并不使人觉得温暖。它在地平线上迟疑了一会儿,抖了一抖,就跌落下去了。一道晚霞从天边升起。
夜幕徐徐降临,雪原渐渐缩小,终于消失在黑暗中。星星一个个地闪现出来。人们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容。长辈们不停地低声叫唤着孩子们的名字,怕的是落下他们中的什么人,被冻死在雪夜里。
根儿觉得自己好像被扣进了一口巨大的铁锅里,他的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他已失去了对它的支配能力,他只是机械地,梦游般地,一脚深一脚浅地朝前走着,生怕落在后面。
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了几声犬吠,这让根儿感到很亲切。他想,“有狗的地方就有人。”他想到他和叔叔从浑河镇逃出来的那个有过一点儿月亮的夜晚,想到老家的草屋,想到自己家干爽的热炕,想到古家庄庄西头儿学校天井里的那些大树,想到他念过的一个个学校。而当他想到“书是念不成了”的时候,觉得很伤心。最后,他想到了他家的那条瘦瘦的懂事的黑狗。“大黑儿怎么样了?它还活着吗?”他悔恨自己去年冬天打过它一回。叔叔家有条身上有着黑白花儿的小花狗儿叫花花儿,那天花花儿与别人家的狗咬架,在花花儿被欺负的时候,大黑儿竟扔下花花儿,自己跑回了家。那天他用柳树条子把大黑儿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训斥它,数落它不该扔下花花儿逃走,骂它是个孬种。从那以后大黑儿就再也没有干过那种背叛逃跑的丑恶勾当。他觉得狗比人好。人里面有汉奸,都鸿勋和黄骗子都是汉奸,但狗是忠实的,里面没有“狗奸”。
“累了吧?”素桂推推根儿的胳膊低声问道。
“不,不累。”根儿从往事的沉思中清醒过来,腿好像也有了劲儿。
“快到了。”素桂低声说。
根儿看见前面有灯光。显然,那里是一个屯子。
“前面就是炮手屯。”素桂习惯地朝前指指说。
“就是咱们要到的地方儿?”根儿问道。
“嗯。”
“不要出声儿!”赵凤山低声关照大家。
“总算到了!可以歇歇啦!”根儿想道,自己走了五十里路,感到骄傲。
胡大珂拉住根儿的手,紧跟在赵凤山的身后。
“要进屯子了,跟紧俺,不要说话!”赵凤山低声命令道。
队伍在屯子的西边停顿了片刻。赵凤山在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就带领大家悄悄地溜进屯子最西头儿的一个很大的院落。这就是赵凤山过去的东家杨大琢磨的大院儿,是他们这一次落脚儿歇息和买粮食的地方。
胡大珂上次跟着赵凤山去的是蛤蟆屯,在炮手屯的北面,离这里大约有三四里路。胡大珂是第一次到炮手屯杨大琢磨家。
杨大琢磨家院子的中央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子的顶端悬挂着一盏灯笼。借着灯笼淡淡的黄光,胡大珂看出这是一个此地常见的财主大院儿,呈长方形。北墙的前面是一排起脊的正房,东西两面各有一排平顶的厢房。正房里亮着灯,厢房黑洞洞的。院落的四个角上各有一座高高的炮楼子,那显然是早年用来防土匪用的,可见这家财主家里养过枪和炮手。从屯子的名字“炮手屯”看,这里是个“出产”给财主们看家护院的“炮手”的地儿,或者曾经有著名的炮手在这里生活过。
赵凤山带领众人钻进了西厢房儿。一股强烈的、暖烘烘的、刺鼻的臊臭气息,扑面而来。根儿不禁嚷道:“这是什么味儿啊!”
从屋里的什么地方传来“咯嘣咯嘣”的声音。根儿听出,那好像是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这声音、这气息都说明,这里是个牲口棚。
“都来啦?”一个男人操山东口音和大家打招呼儿。他手上挑着一个长圆形的、里面有铁丝网的纸糊的灯笼。他模糊的身影映在背后的墙壁上。这时,根儿才看清楚,这里真的是个牲口棚。他们这会儿就站在牲口棚的大门口。牲口棚的右边砌着一道半人多高的老长的矮墙。矮墙后面是一个至少有三个炕那么大的装牲口草的大草池子。池子里面装满了已经铡好的喂牲口的草。草池子的对面儿是一排牲口。
“赵大哥,你们先歇息歇息,我去告诉东家。”打灯笼的男人说。
素桂对根儿耳语道:“他是这里的长工,和俺爹要好,姓梁,大号叫梁永财,俺叫他梁大叔,杨掌柜叫他梁老三,他也是咱们山东人,和俺是同乡,心眼儿挺好。”
“你怎么知道?”根儿问道。
“俺们在这里住过。”素桂说。
根儿觉得素桂懂事,很羡慕她,喜欢听她说话。他想,“姐姐要是还在,也会跟着爹下乡来背粮。她一定比素桂姐姐能干。”根儿想到姐姐,有些伤心。
姓梁的叔叔把灯笼挂在马槽头上的木桩子上,匆匆地离去了。
胡大珂把素桂和根儿抱进草池子里,给他们各挖了一个草坑,让他们坐进去,再用碎草把他们埋起来。根儿觉得渐渐地暖和起来,身上开始有了一点儿活气,脸从冰冷麻木变得热胀滚烫,渐渐恢复了知觉。手和脚又痒又痛,难以忍受。他怕爹知道了心里难受,就一声不响。其实,胡大珂什么都知道。他给根儿脱去布袜,强把他的两只冰块儿一般的脚,放在自己的肚子上面暖着。
“爹,俺的脚不疼了。”根儿说着,就想把脚从他爹的怀里抽出来。胡大珂强把他的双脚摁在自己的肚子上。
过了一小会儿,梁永财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回来了。小女孩儿手上端着一个装干粮用的笸箩。素桂说,她的笸箩里盛的是贴饼子和一些胡萝卜咸菜疙瘩。梁永财跟在女孩儿的后面,一手提着一筐碗筷,一手提着一桶小米粥。
小女孩儿躲在灯影里,好奇地偷偷看着比她小的根儿。
胡大珂领了两份儿贴饼子,打了两碗小米粥,要了两块胡萝卜咸菜。他知道,卖饭是财主的来财之道。他的咸菜不收钱,可是他的贴饼子和小米粥比饭馆里卖得还贵。蛤蟆屯的财主也是这样干的。他听赵凤山说,炮手屯这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儿,天一黑就关板儿了。再者,他们走私粮食,是犯法的,也不敢在街上露面儿,只能在天黑以后进屯。而他们要在漫漫的雪地里东奔西跑劳累一夜,不吃饭是不行的。财主们“琢磨”透了这个理儿,就想出了在这上头再掳这些穷人一把的这个办法儿。他们既卖私粮又卖饭,挣双份的钱。
杨大琢磨,叫杨光文,兄弟四人。他是老大,在家经管土地。二弟杨光华,六年前病故,他的妻子改嫁走人,丢下一个女孩儿。老三杨光武,留学日本,在日本成家,入了日本国籍。四弟杨光明,南满医大毕业,后留学日本,擅长眼科,回国后在城里开办了明明眼科医院。
杨光文爱财如命,而且很有心计。他谁都琢磨,连他老婆的钱他也琢磨。炮手屯一带有很多人吃过他的亏。于是人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杨大琢磨”。要说杨光文,没有多少人知道,提起“杨大琢磨”,这一带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了。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他只有一个女儿,而没有儿子。有人说他缺德,所以连个儿子都没能琢磨出来。
小女孩儿发完了饼子和咸菜,就端起笸箩往回走。走到牲口棚的门口又停住脚步,靠在门框上打量着正在吃饭的根儿。她不明白,他这样小,怎么也来背粮食。根儿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有些不好意思,突然快步走到根儿跟前儿,隔着矮墙,探过身子,把剩在笸箩里的一个贴饼子塞到根儿的手里,抬腿快步走出牲口棚。根儿愣愣地目送着她,感激她的善心,然后把那个饼子一擘两半儿,一半留给自己,一半儿送给素桂。
过了一会儿,听正房里一个女孩儿的声音:“大妈啊,这回来了三个小孩儿。里面有一个挺小挺小的小崽儿,是个小小子儿,比俺都小,挺可怜的!俺送给他一个贴饼子。”
“那个小小子儿好看吗?”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灯影儿里看不清楚。”小女孩儿说。
“你看上他啦?要不要大妈去给你说合说合呀?”中年妇女边说边笑。
“你说啥呢呀,大妈!”小女孩不高兴地大声嚷道。
这时根儿说道:“刚才来的那个小闺女儿心眼挺好,她是谁呀?”
素桂说:“她是东家的侄女,小名儿叫丫蛋儿,大号杨雅范。她爹早就死了,她娘后来嫁人啦,她跟着她大爷大娘过。你没看见她头上系着白头绳儿吗?还戴孝呢。”
根儿没有注意到丫蛋儿戴着孝。
“她念书了吗?”根儿问道。
“听说毕业啦。”
根儿羡慕丫蛋儿有书念。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呢?想到这里,感到伤心。
赵凤山压低声音说道:“有要解手儿的,跟我出去,回来就睡觉。”
草窝儿又宽大,又松软,又暖和,不冷也不热,比睡在鬼屋里的那面又小,又硬,又湿的炕上舒服多了。根儿吃饱了,暖和过来了,困乏压过了浑身的痛痒,在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
“他才八九岁,这么小,真可怜!”素桂看着沉沉睡去的根儿,这样想着,心里也很难受。她把根儿伸到外面的一只手,轻轻地埋进草里。素桂一直盼望着自己会有一个弟弟,可是她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