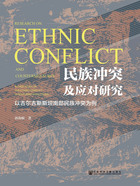
一 研究缘起
(一)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普遍性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大多数多民族国家存在民族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地爆发了多起民族冲突,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地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索马里、科索沃、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印度尼西亚等,其中比较严重的有: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冲突造成50万~10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往国外;1992~1995年波黑内战期间塞尔维亚族、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围绕领土划分等发生的冲突造成20多万人丧生,60多万人致残,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据统计,1945~1999年,因民族冲突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大约为169万人,数倍于国家间战争伤亡的人数。[1]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世界上有5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民族冲突,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12个存在民族问题隐患。[2]1989~2002年,世界上发生了116起主要的武装冲突,其中109起是国内民族冲突。[3]冷战后,民族冲突爆发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并逐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问题的一种常态。进入21世纪,民族与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对国内局势、地区稳定、全球政治格局等造成了明显冲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二)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43年,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民族问题的首个重要著作。此后《共产党宣言》《论波兰问题》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这些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终确立。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等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问题的革命学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民族问题的提法》等著作中提出了“民族”的含义,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与国家学说联系紧密,其立论基础是始终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立场出发来观察和论述民族问题。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的阶级状况、国情、社会性质等都与现在有了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论述上,还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解决民族问题途径的论述上。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提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并引导波兰、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转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5]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6]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主要是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只要阶级消灭了,民族之间对立冲突的根源就消灭了,民族冲突也就随即消亡。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时俱进,提出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自决”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途径。列宁认为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民族问题应服从和服务于阶级问题,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7]列宁主张无产阶级要站在本民族国家的立场来对待民族自决权,不能只赞成某一民族分离而不赞成一切民族分离,这样不利于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也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8]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不同类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同任务,如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等。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提出了民族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论述“俄国的民族问题”时指出,“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9]在此,斯大林列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5种途径:①国家完全民主化,即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斯大林认为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②自决权,即不同民族具有民族自决权;③区域自治,即一定范围内的以民族为单位的区域自治;④民族平等,即民族在语言、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完全平等;⑤民族团结,即斯大林认为的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的相互团结。苏联和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斯大林的思路制定了相应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但历史证明,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为了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毛泽东直言,“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10]“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1]邓小平同样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2]邓小平将两极分化后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放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江泽民也指出,“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13]江泽民认为民族问题包含民族与阶级的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问题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认识都是基于当时的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实践,从“国际主义”“民族压迫”“民族解放”“阶级斗争”“民族自治”等方面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冲突”的认识是宏观的和“粗线条”的,对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爆发过程、事件影响等的认识缺乏预见,对民族冲突的爆发原因、动员过程、升级途径、事件后果、政府处理等更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卢旺达等)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民族问题,我们显然不能继续用“阶级斗争”“民族压迫”“民族解放”等的眼光来审视和解读,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完全是“殖民地国家对被殖民地国家的压迫”“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与时俱进,近年来,民族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逐渐凸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既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使命和担当。
(三)“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民族冲突
安全始终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和基本利益。邓小平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江泽民曾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历来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后,不仅设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保证国家安全明确列为头等大事”。习主席多次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各项工作。”
反观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内忧明显大于外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国内安全”重于“国际安全”的观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根据哲学的“内外因理论”推导出来的学术结论,而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严重甚至严酷的现实。如果对此再熟视无睹、漠然置之,那么它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变成直接的危害。[14]
在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忧”中,“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无疑是影响范围最大、影响后果最严重的因素:在我国所有受“三股势力”影响的地区中,新疆无疑又是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地区。近年来,由疆内外分裂势力发动的暴力恐怖事件的频度和强度都明显增加和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3月到2014年7月由于暴恐事件死亡的人数就高达311人(见表0-1),其中有震惊中外的“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3·1昆明严重暴恐案件”“5·22乌鲁木齐爆炸案”,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
近年来的诸多事实表明,“三股势力越来越多地融为一体,成为极端-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15],“三股势力”合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作案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很有可能发动以“民族冲突”为主要形式的突出公共安全事件,以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秩序、分裂国家领土的目的。而民族冲突一旦发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新疆的稳定局势,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会危及公共秩序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形象等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新疆工作。2013年以来,习近平对新疆工作先后做出多次指示和批示,部署维护新疆稳定和反新疆分裂问题的工作。2014年4月,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014年5月底,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2017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表0-1 2013年3月到2014年7月新疆内外暴恐事件一览

2007年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在《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中强调,“建立反映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建立以信息资源集成为基础的统计、分析、评价、监测、预警和决策咨询系统”[16],这是中国首次提出要建立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随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始部署建立中国国家民族关系预警体系的各项工作。2012年7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在《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进一步提高对民族关系分析评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能力”。[17]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民族关系如何评估,民族冲突如何发生、如何预警、如何防控还没有成熟的思路和有效对策。
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民族问题,许多学者的研究仅限于进行概念的考究、民族实体的细化、民族关系的评析,对民族冲突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对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书选取了民族问题中的民族冲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突发民族冲突爆发的原因、过程、政府应对等,以期对我国防控民族冲突等公共安全事件提供有效启示。
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民族冲突数量庞大、模式多样,但从“民族冲突”本身的逻辑结构来讲,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书选取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作为研究案例。
(四)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的典型性
2010年6月10~15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和巴特肯州发生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民族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书之所以选取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以下几方面。
(1)多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对“三股势力”在该地区的活动方式、活动范围、作案手段等具有一定的把握,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可以为新疆防控“三股势力”发动民族冲突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供有益借鉴。
(2)到目前为止,国外多个组织和机构(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国际危机组织、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等)已经掌握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爆发的详细过程,这可以作为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的前期资料。
(3)民族冲突从酝酿、动员、爆发、升级进而转入低潮,具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民族冲突爆发过程中的导火索、持续时间、冲突空间、打砸活动、强奸行为等也具有特定的规律,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从“民族冲突自身的规律”上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本书选取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作为案例,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的爆发原因、发展过程、政府应对的教训和如何构建民族关系评估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等,对我国防控民族冲突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