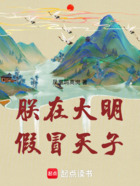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52章 朱祁镇开始黑化
袁彬刚踉跄着攀上城头,一阵狂风又迎面扑来,他下意识抬手遮挡,却见大同城外已然天昏地暗。
狂风卷着戈壁的砂石,在旷野上掀起滔天浊浪,那风来得极凶,裹挟着碎石砂砾拍打在城墙之上,发出噼啪作响的声响。
连绵的烽燧在风沙中若隐若现,时而如鬼魅般浮现,时而又被黄沙吞没。
城下枯死的胡杨在风中疯狂摇摆,枝干发出凄厉的哀鸣。
风沙过后,天地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浑浊的沙雾。
城墙上的旌旗、垛口间的守军、地上的兵器,无一例外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沙,宛若出土的文物。
故而当朱祁镇的身影在沙尘中渐渐显现时,他蓬头垢面的模样与周遭被风沙洗礼的一切堪称浑然一体,形成了一种异样的和谐。
风沙掩盖了贵贱的界限,在这塞外边城,人人皆是满面尘灰。
因此没有人怀疑皇帝为何会如此狼狈不堪、面容憔悴,更没有人敢去猜测,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大明皇帝,竟会被虏酋那般欺凌。
广宁伯刘安在城垛间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朱祁镇身着瓦剌服饰,但那清癯的面容与挺直的脊背,分明就是他曾多次在朝会上瞻仰过的天子。
刘安喉头一哽,竟连行礼问安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虚扶城墙,泪流满面。
在朱祁镇身后,伯颜帖木儿麾下的二十余名亲信整齐肃立。
这些方才还对大明皇帝肆意嘲弄的瓦剌士兵,此刻却在伯颜帖木儿的严令下,不得不摆出恭顺姿态。
他们铁甲森然,腰佩弯刀,远远望去,倒真像是一队忠心护主的御前侍卫。
只是那偶尔闪动的阴鸷眼神以及与汉人截然不同的粗犷面容,暴露了他们真实的身份。
朱祁镇先前远远望见袁彬入城,紧绷的心弦顿时为之一松,待见到城头的广宁伯刘安时,这位饱经磨难的帝王再也抑制不住心绪。
他顾不得再端什么皇帝架子,急切地向前几步,朝城上挥手高呼,“刘卿!刘卿!是朕啊!是朕啊!”
朱祁镇向前迈出几步,身后那二十名瓦剌士兵便立即如影随形地跟上几步。
他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不敢超前一步冒犯天威,也不敢落后半步违背军令。
刘安涕泪纵横多时,渐渐注意到那些瓦剌士兵始终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圣驾。
他再迟钝也觉察出其中必有蹊跷,自是不敢擅开城门,只得朝城下高声喊道,“陛下勿忧!臣这就出城迎驾!”
朱祁镇闻言神色微动,刘安只说“出城迎驾”,却对袁彬叫门时提出的“速开城门”避而不提,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一抹苦涩在心头漫开,却仍强自展颜,扬声应道,“甚好!刘卿忠勇可嘉!遣一个城中会说蒙语的通事,随你一道出来!”
城头众官员交头接耳商议良久,果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与也先结有姻亲的大同通事指挥李让。
李让面如土色,连连摆手推辞,“镇宪(对总兵官的尊称)啊,下官与大同王是儿女亲家不假,可若此番谈判时瓦剌提出非分之请,朝廷不应,那也先将来定会杀了下官!”
他边说边往人后躲闪,额上冷汗涔涔而下,官袍后背已然湿透一片。
袁彬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攥住李让系腰,力道之大几乎要将人提起,“圣驾就在城外风沙中苦候,尔竟敢推诿?你既怕得罪也先,难道就不怕触怒天威么?”
刘安见状,立即沉声附和道,“陛下在瓦剌这些时日,想必早已知晓你与大同王的姻亲之谊,今日你若执意不去,岂不是坐实了通敌之嫌?”
李让对皇帝在瓦剌的艰难处境一无所知,此刻听得刘安这般言语,心头骤然一紧。
倘若圣驾回銮,追查此事,自己轻则丢官罢职,重则下狱问斩。
思及此处,他脊背发凉,只得狠狠一咬牙,硬着头皮应下了此事。
于是大同城又放下了吊桥,刘安与袁彬、李让一起,三人一同出城去见朱祁镇。
刘安与皇帝情谊深厚,甫一见面,便伏地叩首,再度声泪俱下。
袁彬与李让亦随之下拜,却唯有刘安哭得肝肠寸断,连朱祁镇也被牵动心绪,眼眶泛红,几欲垂泪。
待刘安哭声渐歇,李让便与那同为通事的忠勇伯蒋信以蒙古语寒暄数句。
二人对答如流,口音纯正,既全了礼数,又教四周瓦剌兵卒听得真切,两边翻译俱无错漏,并无欺瞒之嫌。
双方礼毕,朱祁镇便迫不及待地道,“先前在宣府,朕屡叩城门,而杨洪拒不开迎,今日刘卿出城相迎,忠义可鉴!”
他喉头微动,似有千言却只化作一声长叹,“朕且问你,朕在宣府时,曾写过一道圣旨投入城中,这道手诏,可曾送达朝堂了?”
刘安刚刚哭过一场,面上泪痕未干,一听这话,冷汗“唰”得一下就下来了。
但面对君父,他不敢说谎,只能低垂着头含糊道,“大司马(兵部尚书尊称)说那是胡虏‘假传圣旨’……”
“大司马?!什么大司马?哪里来的大司马?”
朱祁镇心下一跳,一把抓住刘安的衣袖,慌忙追问道,“兵部尚书邝埜随朕亲征,已然于土木堡殉国了!这朝中哪里又冒出来另一个大司马?”
刘安小心翼翼地回道,“回陛下,是……是于廷益(廷益是于谦的字),今日刚下的郕王谕令,升兵部左侍郎于谦为本部尚书……”
听到现任兵部尚书是于谦,又见诏令是出自“郕王谕令”而非“陛下圣旨”时,朱祁镇陡然紧绷的肩背瞬间松了几分。
毕竟于谦也是明宣宗为他留下的老臣之一,这些年于谦为官清正,素有贤名,可谓人所共鉴。
想到此处,朱祁镇竟莫名感到一丝欣慰,值此动荡之际,朝中有于谦这般能臣执掌兵部,未尝不是社稷之幸。
更何况,这任命是出自他那一向温厚怯懦的郕王弟弟。
朱祁镇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他的第一反应是,这般安排,必定是出自孙太后的手笔,不过是碍于“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才借郕王之名行事罢了。
这时的朱祁镇压根就没往“权臣擅政”那方面去想。
毕竟在他的记忆中,于谦那张永远古板方正的脸上,只有“忧国忧民”与“犯颜直谏”这两种神色,从来就写不出“野心”二字。
这个执拗得近乎迂阔的老臣,是定会恪守大明祖制,迎他回朝的!
朱祁镇脸上又浮现出笃定的笑意,“好,好,母后殿下圣明,若非要择一兵部尚书,满朝文武再无比于卿更妥当的人选了,纵使是朕亲点,也必定属意于于谦。”
刘安见朱祁镇这般气定神闲,觉得皇帝大概是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他看了看围在四周的瓦剌人,终是咬牙趋前半步道,“陛下容禀!此非出自皇太后殿下懿旨,实乃郕王殿下独断。”
“本月十八日,皇太后殿下已明发诏谕,命郕王殿下总理朝政,凡六部奏章、百官庶务,皆需启禀郕王殿下定夺。”
此言一出,朱祁镇面上笑意骤然凝固。
他太了解自己的母后了。
孙太后虽素来谨慎,但昔年宠冠六宫之时,也是敢与胡皇后争金宝的彪悍女人。
即便碍于祖制,她不能直接涉政,可在这等生死存亡之际,她是断不会轻易将权柄尽数付与郕王的。
这里面肯定有哪里出了问题。
刘安见皇帝神色阴晴不定,心知圣驾久困塞外,于朝局已如隔雾看花。
当下再顾不得君臣礼仪,赶忙将这短短几日的惊涛骇浪同皇帝娓娓道来。
南迁之议如何甚嚣尘上,郕王与于谦如何在朝堂上力排众议;孙太后如何立皇长子为储、命郕王监国;于谦现下又如何昼夜不息地调兵遣将,筹备京师保卫战……
每一句话都像丧钟轰鸣,敲在朱祁镇的心头,震得他耳膜生疼。
其实朱祁镇何尝不明白,郕王监国、于谦主兵,是社稷危亡时的明智之举,孙太后的折中立储之策,更是老成谋国。
此刻刘安敢在瓦剌人面前直言不讳,掷地有声地道出这一连串变故,恰是最有力的明证。
大明终究是大明。
大明并未因土木堡之败而仓皇弃都南逃,亦未因战场折损而丧失反击之力,只要上下同心,必能固守京师。
更何况朝中已立储君,并有成年亲王坐镇,即便天子被俘,社稷亦无倾覆之虞。
可这些念头越是清明,胸口那团血肉就绞得越发狠厉,那锥心之痛,一阵紧似一阵,几乎要将他整个人撕裂开来。
仿佛有人将他的心脏生生剜出,摆在奉天殿的龙椅上供人观赏。
那淋漓的鲜血,正一滴一滴,溅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版图之上。
刘安话音方落,却见朱祁镇身形一晃,跌跌撞撞地倒退了两步,正撞到那伯颜帖木儿的怀中。
刘安惊得魂飞魄散,慌忙上前搀扶,却被皇帝枯瘦的手腕一把格开,“朕知道了。”
“好个于谦,好个郕王,倒是替大明寻了条活路。”
皇帝惨笑一声,唇边挤出几道刀刻般的纹路,“昔年王振罗织罪名,曾将于谦下狱三月,这一回,于谦可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了,当真是天道好轮回。”
刘安知道皇帝心里不痛快,眼下他是既不敢骂王振,也不敢夸于谦,只能讪讪应道,“是陛下仁德,当年开恩赦免了于廷益,否则他岂有今日之显贵?”
朱祁镇默然片刻,眼底掠过一丝冷峻与清明,竟显出几分久违的帝王气度。
但听他淡淡回道,“胡说!于谦是难得的忠臣,是国之栋梁。”
“当年他被囚狱中时,数千百姓联名上书,恳请其留任,他是天下公认的能臣、清官,是朕……是朕耽误了他这么些年。”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远处,似是在看那紫禁城的巍峨宫墙,又似是在看那朝堂上的风云变幻,语气平静却透着苍凉。
“如今他得郕王器重,总算是扬眉吐气,只怕从此之后,他心中已是再无朕这个君父了。”
朱祁镇此时满身尘沙,胡服裹身,乍看之下哪还有半分天子威仪,便是比起身后那些瓦剌士兵也显得落魄三分。
可偏偏就是这般狼狈之态下,他轻描淡写地吐出两句话,既无雷霆之怒,亦无厉色呵斥,甚至就连语气也平和得近乎寻常。
刘安却被吓得双膝一软,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朝皇帝叩首道,“陛下明鉴!朝中厉兵秣马,实为社稷安危,绝非……绝非是有意要将圣驾拒于国门之外啊!”
伯颜帖木儿顿时对朱祁镇刮目相看。
这小皇帝可真了不得!
明明已成阶下之囚,日思夜想地盼着回北京,此时骤闻朝中变故,非但没有失态,反而仅凭随口两句话就能将刘安这等镇守一方的勋贵子弟震慑得汗出如浆、魂不附体。
看来这大明天子的分量,远比想象中的还要重得多啊。
伯颜帖木儿嘴角微扬,露出几分得意之色,不愧是老子相中的人物,果然非同凡响!
朱祁镇冷眼看着刘安连连叩首,待其额头已然见红,方才心满意足地唤他起身。
此刻他已心如明镜,这北京一时半会儿是肯定回不去了。
既如此,便须在这千里之外的漠北,牢牢维系住朝堂之上的影响力。
眼下瓦剌大军压境,于谦借社稷安危之名,行拥立郕王之实,自是名正言顺。
就连孙太后,也只能以立储这等权宜之计,来保全他这个身陷敌营的皇帝。
可待到他日胡骑北退,狼烟平息,于谦与郕王今日之所作所为,又当以何等名目自处?
朱祁镇在心底反复推演着种种可能,若非谋朝篡位,便只能是正统帝驾崩、太子夭折,最终帝位兄终弟及,落入郕王之手。
毕竟郕王坐镇京师,御敌有方,英明神武之姿远胜他这个兵败被俘的昏君。
一念及此,朱祁镇只觉得胸中血气翻涌。
不!朕绝不能将这大明江山拱手让给那个庶出子!
凭什么?
凭什么朕在这漠北苦寒之地受尽屈辱,他却在京城安享尊荣富贵?
凭什么他既能捡这天大的便宜,又能赢得万民称颂、百官拥戴?
他在心底暗暗咬牙发誓,朕定要在瓦剌好好活着,无论如何也要活到重返北京城的那一日!
届时,定要叫天下人知道,谁才是真龙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