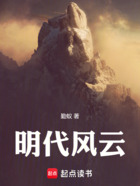
第18章 从此飞禽变走兽
“胡闹!”景泰帝又忍不住出口呵斥。
不知为何,每次见到这个儿子,心中总会莫名窜起一股无名火。
他深吸一口气,强压怒意,耐着性子训诫道:
“自古以来,文武分途,各司其职!
文官以科举取士,专掌民政、钱粮、刑名;
武将则凭世袭军职或战功晋升,统兵征战、镇守四方。
商辂虽为我朝三元及第的状元,才华横溢,办事老成持重,为人清正勤勉,且在兵部任职多年……”
说到此处,景泰帝自己说着说着忽然停了下来,眉头微蹙,竟隐隐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站不住脚,若抛开“文武殊途”的成见,商辂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行?
毕竟,历朝历代虽讲究文武分治,但到了本朝中期,这条界限早已不如开国时那般森严。
随着“重文轻武”之风渐盛,文官集团权势日增,朝廷偶尔也会破例让文人涉足武职。
譬如于谦,堂堂兵部尚书,不也统领三军,指挥京师保卫战?
而锦衣卫不过区区六千余人,比起千军万马的战场调度,反倒显得简单许多……
“陛下圣明!”
宁阳侯陈懋再一次跨出队伍,并朝前迈进了两步,厚重的朝靴在地砖上踏出沉闷的声响,花白的胡须随着激动的语气剧烈颤动。
“自古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此乃天道伦常!”
他刻意将“天道“二字咬得极重,浑浊的老眼却斜斜瞥向朱齐所在的方向,“即便是东宫储君,也当恪守祖宗成法,岂能...咳咳...越俎代庖?”
朱齐冷眼旁观,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清楚地记得史料记载:
正统十四年,陈懋在宣府冒领军功、杀良冒功,本该问斩。
得知此事的英宗亲自下特旨赦免了其罪,就是这份救命之恩,倒让这位老将成了南宫最忠实的拥趸。
此刻陈懋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表面上是在维护所谓的“天道纲常“,实则在暗指责他朱齐年少无知、不谙朝政。
殿内群臣屏息凝神,目光在这几人之间来回游移。
忠国公石亨依旧巍然不动立于殿中。
如今京营虽已在于谦主持下改制为十团营,但这位执掌京营多年的老将,仍然司职督操十营军马,且其麾下亲信子弟占据各营坐营官要职,可以说超十万精锐尽屯京师。
纵使天下兵马名义上归兵部与五军都督府统辖,可在石亨眼中,锦衣卫这区区数千之众,不过螳臂当车。
若非存了替族中子侄谋个前程的心思,今日他本不屑开这个口。
只是太子今日所言石彪之过,倒是让他心生一丝警惕。
随着宁阳侯的搅局,形势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朝臣嘀咕的对象从朱齐换成了这胡子花白的老将。
这时,商辂从文官队伍中快步出列,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对着御座之上的景泰帝叩首道:
“臣愧对陛下隆恩!自任兵部左侍郎以来,臣夙兴夜寐,兢兢业业,仍恐本职工作有所疏漏。
今锦衣卫指挥使一职干系重大,臣才疏学浅,实在惶恐难当此重任!恳请陛下另择贤能之士。”
由于方才被上面注视了一眼,商辂实在担心陛下疑心这些谏言是自己在背后授意,误认为是他在借太子之势谋取私利,那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另外,他寒窗苦读十数载,梦想一直是位列三师,内阁首辅,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青云之路,光耀门楣的正途。
虽说是从兵部左侍郎的副职转为锦衣卫指挥使正职,但终究是武职,而且都只是正三品,又要掌管臭名昭著的南北镇抚司。
一想到此处,商辂便觉得心中有些别扭。
眼看景泰帝之前已经有所动摇,却被陈懋这一番说辞再度搅乱,导致商辂亦心生抗拒之意,朱齐在一旁看得有点慌,生怕再出变故。
他心知商辂这般抗拒,要么是对锦衣卫这等特务机构心存芥蒂,要么仍是那套“文尊武卑“的迂腐之见作祟,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不愿自降身份,踏入武臣之列。
朱齐决计不会就此放弃,让陈懋这个老家伙得逞。因为对于他来说,商辂是为数不多安全评级为B的选择。
他再度走上前去,朗声道:
“《皇明祖训·持守篇》有云:祖宗之法,当守其本;若时势有异,亦许变通施行。
如今瓦剌虎视于北疆,倭寇战船游弋东海,中原腹地蝗灾旱灾连年,实乃危机存亡之秋也。”
他微微抬头,目光坚定地望向御座:
“昔年永乐朝,文渊阁大学士杨荣临危受命,总督各大军务。
景泰元年,兵部尚书于谦——于尚书更是一肩担起京师防务。
此皆文臣掌武事而建功立业之明证!”
说到此处,朱齐朝着于谦拱拱手,随而转向宁阳侯,语气渐冷:
“老侯爷久在军旅,竟不知此等典故?若见识止于此,还是莫要再妄议朝政为好。”
说完,他再次深深拜下:“儿臣恳请父皇以社稷为重,破格用人,此乃顺应天时之举。伏惟圣裁!”
朱齐话音方落,宁阳侯陈懋那张老脸顿时涨得发紫,显然是被这番话气得够呛,鼻子冷哼了一声,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只见景泰帝御座前慢慢踱步,一言不发。
朝臣们屏息凝神,谁都不敢出声。
该举荐的人选早已反复争论过数轮,景泰帝不想再征求大家意见了,再议下去无非是徒增口舌之争。
景泰帝本来在用人上便比前几任皇帝大胆许多——在他治下,因地方政绩卓异而被破格擢入中枢的官员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其他时期基本上极为罕见。
锦衣卫指挥使一职,必须由心腹担任。
原本陈循力荐的石彪确实是个合适人选,但经太子方才那番话,景泰帝心中也不免生出几分猜忌。
他暗自盘算:
昔日郕王府的旧部,如今皆已身居要职。
而登基后朝夕相处的肱股之臣,又基本上都是二品以上的重臣。
这个正三品的职位,竟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其余的人选么,中军都督府的王江,其性好猜忌,遇事多退避,难以担当这锦衣卫指挥使之任。
羽林左卫的杨连光倒是文武兼备,但为人好议论,遇事喜欢到处说,是个藏不住话的,显然不能执掌宫廷禁卫这等机要职务,
这么想想确实也没什么好的人选。
商辂这位年轻的臣子是他一手提拔的,状元及第之后不过四年便召他入阁参与机务,办事向来稳妥。
先前是自己拘泥于“武职当用武将”的成见,和这无知的宁阳候一样,被这一叶障目。
如今商辂又辅助于谦打理兵部,对军务倒也不算陌生。
反观今日太子提及的现下乃危急存亡之秋,倒是有几分道理。
“内阁拟旨!”
景泰帝突然驻足,声音打破殿中的寂静。
“商辂即日调任锦衣卫指挥使,不得有误。
原兵部左侍郎之职,由右侍郎孙原贞递补。”
朱齐反应极快,当即撩袍跪地,额头重重叩在地砖上:
“父皇圣心独裁!天恩浩荡!”
陛下的圣裁既下,便是金口玉言,再难更改。
商辂只觉得喉头一阵发苦,仿佛被人强塞了一嘴黄连。
他今日早朝并无要事上奏,所以站在那里吃了一早上的瓜,没想到最后竟然吃到自己身上,不禁苦笑起来。
只见商辂缓缓跪伏于地,叩首道:“臣——领旨谢恩!”
起身时,他下意识抚了抚胸前的补子,想到从此文官的仙鹤要换成武职的猛兽,这般变化让他觉得有些不适。
商辂暗自决定,在这身飞鱼服未脱之前,决不踏足故乡一步,他丢不起这个脸。
内阁首辅陈循的脸色同样难看。
他本想着借此机会向忠国公卖个人情,中间连石亨本人都亲自下场助阵,谁知陛下竟半点情面不给。
这个结果,着实也让他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