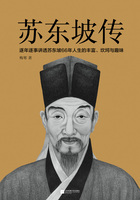
第6章 《变法风暴》:回京就职,妻亡父丧
与三年前来凤翔一样,苏轼再次在天寒地冻的季节离开。自凤翔一路向东,往京城汴京而去。一路风雪泥泞,却挡不住苏轼回程的热情。
一个归心似箭的游子,寒风吹面不觉寒,日行千里也嫌慢。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返京,一家人终得团聚。
家中一切如故,堂前的芦、砌下的竹、堂后的石榴树、院子里的双柏及葡萄架……它们都还在,与三年前苏轼离开时没有多大区别。父亲在庭前开了一方水池,清澈的细流正从假山岩鼻中汩汩而下。
站在无比熟悉又陌生的院子里,看到颤巍巍迎向他的老父亲,苏轼不禁泪盈两眼。三年来,他不清楚自己有多沧桑,却发现父亲已经成了一位发白背驮的老人。
奉诏命,回京不久,苏轼就到新的岗位报到了。这一次,他被派到登闻鼓院当差。听书看戏,常见受了冤屈的百姓高喊着“冤枉啊”,将堂前大鼓击得砰砰作响。苏轼就被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但他不是坐堂的青天大老爷,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表疏文。
不管是论朝政得失,还是沉雪鸣冤、检举官吏,皆可到登闻鼓院击鼓递状。苏轼当初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取为三等,现在这个差事也算对路。
英宗却觉得,给苏轼安排这么个差事有点委屈他。对于苏轼的文名与才名,他早有耳闻。苏轼在凤翔的政绩,他也有所了解。循唐代先例,英宗想特召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的要职,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率先反对的是宰相韩琦。韩琦的大意是:苏轼才大器大,他日自当为天下用,但眼下朝廷还不能急于求成,要加以培养,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于他。等到天下之士无不想朝廷重用他的时候再重用他,谁也说不出什么来。现在贸然重用,怕不能服众,对苏轼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英宗不甘心,继续道:“且与修注如何?”
修注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也是多少士子向往之职。对于此差,韩琦再次否决。他建议英宗还是按照一般通例,先召试学士院,再与馆职。
韩琦的做法,到底是出于私心更多,还是君子之爱更多,且不去追论。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学霸”,任何考试对于苏轼来说,都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在那次学士院召试中,苏轼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选,优诏直史馆。苏轼没靠英宗眷顾,凭自己的实力说话。
从满目黄沙的凤翔重返宫阙林立的帝都,仿佛人间天上;如今,学士院的召试又如此顺利,苏轼再不用于风沙雨雪里四处奔波。皇家帝苑深处的秘阁里,虽无人可以把臂纵论古今,但所谓大隐隐于朝,在喧嚣的政坛之中,若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不亦强过那些唱高调的假隐士吗?
苏轼既已回京任职,他可以接过苏辙照顾父亲的重担了,苏辙也可以放心外任。
其实,苏轼重返京城,舒心的日子并没过太久,漫天的愁云惨雾就四下逼来。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苏轼二十七岁的妻子王弗突然因病去世,给他留下一个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
这于苏轼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那段日子,苏轼被撕心裂肺的痛彻底吞没了,眼前晃来晃去的全是王弗的模样:她低头绣花做针线的样子,她含笑听他讲话的样子,她不疾不徐劝他交友须慎的样子,她低眉听他读书的样子……
往事历历,悲喜交织。回首这十年来他们走过的路,从眉山到京城,从京城到凤翔,再从凤翔重返京城,王弗跟着他吃过多少苦、担过多少心,又给过他多少提醒与帮助。如今安稳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她却匆匆离去。
王弗客死他乡,灵柩只得暂时停放在京城西郊。
王弗的早逝,对苏轼父亲的打击也非常大。他痛心地叮嘱儿子道:“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
王弗对婆婆程夫人敬爱有加,程夫人生前如此,程夫人走后依然。王弗同婆婆一样深知苏轼的脾性,他太刚,又太率性,这样性格的人,行走于官场是会吃亏的。所以,王弗如婆婆在世时一样,不时给苏轼以提醒。
苏轼对文物收藏及炼制丹药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苏家所居院子里的大柳树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地方始终存不住雪。天晴之后,地面还隆起了几寸。苏轼的好奇心被勾起,他怀疑下面可能埋有丹药——丹药性热,故不能积雪。
苏轼找来工具,欲挖开看个究竟,却被王弗一句话给止住了:“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当年在眉山纱縠行街的院子里,母亲程夫人就曾制止家人去挖掘埋于地下的一只大瓮。
王弗的话,让苏轼惭愧罢手。
如今,再无人会在他说错话、办错事时直言提醒,也无人会在他疲倦不堪时温言抚慰。
封建时代的夫与妻,夫为妻纲,妻如衣裳。难得的是,苏轼与王弗在精神世界里相互欣赏,彼此依赖。对于苏轼来说,王弗已不仅仅是妻子,更是精神支柱。
苏轼对王弗的那份思念,从此如影随形。
眼前,苏轼还处在绝望与哀伤里,他哪里会料到命运之神已经再次向他露出狰狞的獠牙。就在王弗去世仅十一个月后,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父亲苏洵又因病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丧妻又失父,人生两大至痛,苏轼在一年之内尝尽。
苏洵的去世,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轰动。英宗诏赐银、绢,苏轼请辞,为父亲求赐官爵。六月九日,朝廷诰赠其为光禄寺丞,同时特饬有司备船只,载送苏洵灵柩回蜀。
七年之前,苏洵带领儿子儿媳辞别家乡,奔赴京城,一路虽历经艰辛,但还是完整而融洽的一家人。而今,兄弟俩却是披麻戴孝,扶着老父少妻的灵柩南返。其心情之苦,真是无以名状。
治平四年(1067)十月,兄弟二人合葬父母于武阳县(今四川眉山彭山区)安镇山之老翁泉,王弗就安葬在旁侧。苏轼将王弗的墓穴凿为二室,希望百年之后能与她死而同穴。
从治平四年(1067)一直到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都在蜀中老家替父守制。
守丧期满,苏轼续娶王闰之为继室。王闰之是青神县王介幼女,是发妻王弗的堂妹。
岁末,兄弟二人又要还京了。这一走,何时再回来,谁也说不准。家中无人,但是祖坟需要人修护照看,一些田宅也要打理,还有亲戚间的人情往来。这些事,苏轼一并委托给了与他们一起长大的老邻居杨五哥(济甫),如遇大事,则由堂兄子安做主。
一入宦途深似海,从飞离故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四海为家,终生漂泊,再没能回去,故乡成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
苏轼兄弟料理好家事后,携家眷重返京城。此时的京城,一场惊涛大浪正在掀起,苏轼兄弟也将无法避免地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浪的旋涡中……